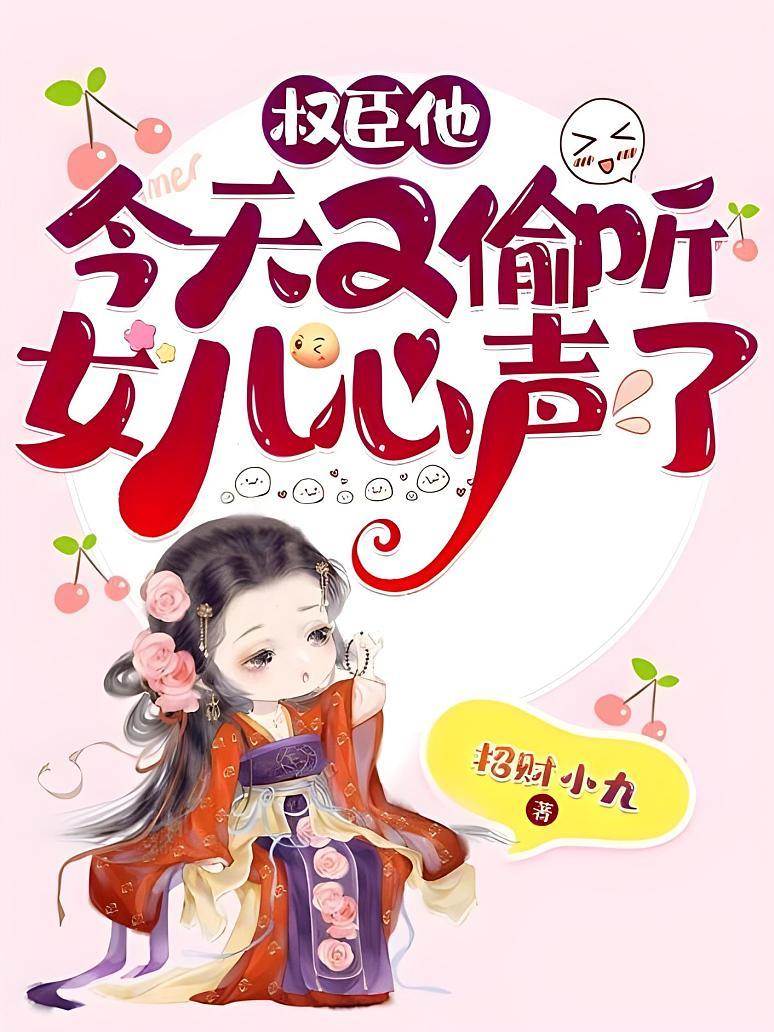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明朝好丈夫》 第140章 金冊
朱覲鈞不由笑了,擺了個舒服的坐姿,含笑道:“這些人,連爪牙都算不上,只不過是父王偶爾贈些禮出去,讓他們爲父王說話而已。宸濠,父王若是靠這些人,早已骨無存了。凡事,靠的是我們自己的人。他們本就是趨炎附勢之徒,你又何必怒?”
見父王笑的自信滿滿,朱宸濠不問:“那父王所說的好是什麼?”
朱覲鈞目一閃,淡淡道:“其一,柳乘風是你我大敵,也是那蕭敬的敵人,蕭敬爲人雖然豁達,可是他非殺柳乘風不可,柳乘風一日不除,秉筆太監和東廠廠公的威嚴就然無存,連東廠,也難以維持下去。這個人一旦了殺機,就會不擇手段,難免會讓你我父子漁翁得利。”
“這其二嘛……”朱覲鈞笑的更加深沉,慢吞吞的道:“你我父子在殿中與太子反目,這是好事……”
朱宸濠不由的道:“這也是好事?”
“當然。”在朱覲鈞從位上站起,負著手,在這屋子裡來回踱步:“宸濠,你還是太年了,有些事,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你我父子雖是面大失,可是卻可以讓那朱佑樘便是對我們在南昌做的事起了疑心,也絕不會輕易手。你想想看,現在天下人都知道,你我與太子已水火之勢,皇上對我們,只會安,絕不會再挑釁,就算他懷疑我們有什麼作,也絕不敢大張旗鼓的查探,你可知道爲什麼?”
朱宸濠想了想,眼睛一亮:“他就算是查,天下人也只會說,皇帝是爲太子張目,爲了太子,而欺凌宗室?”
在朱覲鈞笑了,道:“正是如此,換做是別人,倒也罷了,可是當今皇上一向惜羽,怎麼可能爲了一點蛛馬跡,而壞了自己的聲名,畢竟,我們是宗室,這欺凌宗室之名,卻不是他能消的。爲父這些年來,夜夜輾轉難眠,爲的,便是怕許多事被東廠、錦衛偵知,現在卻是等於有了一個護符,往後我們在南昌的計劃,可以再快一些了。”
Advertisement
“你等著瞧吧,皇帝爲人最懂得收買人心,現在我們與他的太子反目,他不但不敢報復,反而會對你我更加優渥,讓大家知道,他爲人公允,不會偏袒自己的兒子,我們在京城也呆了這麼久,聽說趙門外二十里,靠近通州的地方有一桃林,此時雖是秋風蕭瑟,可是據說那裡,酒旗林立,站在酒肆裡登高遠,向北,可見京師,向南,則可一覽通州,這句話雖是言過了些,不過我們索無事,明日就去看看。”
“現在又不是桃花盛開的季節,去那裡喝酒做什麼?”朱宸濠皺起眉道。
朱覲鈞卻是搖頭,道:“爲父之所以去那裡,你以爲只是去看禿禿的桃林嗎?爲父是想看看咱們在通州的生意。”
“生意……”朱宸濠恍然大悟。
這天下的通州有兩個,一個在江南,一個在京城南郊,所以便有了南通州、北通州之稱,這兩個通州卻是一點都不簡單,因爲分別是京師連接江南的大運河起始點和終點,每年,無數的漕船從南通州出發,抵達北通州,再將無數的錢糧賦稅,經過道由朝門進京師。
所以說這大明的天下,南北通州未必最爲富庶,可是若說商賈雲集,人流如織,卻非這南北通州莫屬,據說但凡是生意到了一定程度的巨賈,都會在南北通州租用貨棧或是門臉,否則定會被人小視。
朱宸濠道:“父王的意思是……”
朱覲鈞淡淡一笑:“南通州父王已經安了人手,唯有這北通州,父王卻還只是人正在收買籌措,若是能將南北通州納手中,將來若是有事,這錢糧還需擔心嗎?”
朱宸濠深吸了一口氣,南北通州這兩地方,可謂是天下最至關要的樞紐,甚至可以說,大明可以沒有南京,沒有蘇杭,卻絕不能沒有南北通州,誰若是悄悄掌控了這裡,且不說富可敵國,就是一旦有事,讓人堵塞住這運河要道,放一把火,沉一些船,也可以堵塞住南北之間的水道數月,燒掉江南一個月的賦稅,別看只是這麼一小會兒時間,可是真要做起什麼大事來,這點兒時間卻是足夠了。
Advertisement
正說著,外頭有隨扈稟告,道:“王爺、殿下,宮裡來了人,遞了個本金冊來。”
父子二人停止了談,朱覲鈞一副淡然之,捋須道:“進來。”
那隨扈進去,將一本金冊在朱覲鈞的手裡,朱覲鈞接過,隨即翻開了一下,不由莞爾笑道:“父王竟差點忘了,再過幾日,就是皇后娘娘的誕辰,宸濠,你看,這是皇上和皇后娘娘請你我二人宮祝壽呢。”
朱宸濠不道:“祝壽?”接過金冊看了一會兒,隨即哂然一笑:“這又是我們父子宮去給皇上演一出宗室和睦的戲碼了。”
朱覲鈞想了想,篤定的道:“我們要去,不只是要去,而且還要備上一份大禮。”
朱宸濠不道:“這又是爲什麼?”
朱覲鈞鎮定自若的道:“我們和太子反目,可是反目歸反目,這皇后娘娘卻還是要結一下,結,是要讓人知道,你我父子二人心寬廣,不過若是我們送的壽禮比那太子更厚,那太子會如何?”
朱覲鈞眼眸一亮,冷笑道:“讓太子那草包出醜,也教天下人看看,這皇后雖是太子生母,可是卻還不如父王和兒臣對皇后更有心意。”
朱覲鈞微微一笑:“只是送什麼禮好呢?”
朱宸濠遲疑了,猶豫片刻:“據說娘娘好彈琴……”
父子二人,同時出古怪的笑容。
“而且這一次,說不定連那柳乘風也會去,他不過是個小小百戶,卻和太子走的近,父王,我倒是有一個法子,可以讓這柳乘風死無葬之地。”
………………
從宮中出來,柳乘風並沒有急著回家,不過已經了鄧龍,幫忙先去知會一聲了,至於他,則是僱了一輛馬車,飛快往百戶所去。
Advertisement
柳乘風倒不是不想念家裡的妻子,只是他這時候還有一件事去做。
僱來的車伕倒是健談,一見柳乘風從午門附近出來,以爲遇到什麼貴人,便問柳乘風是哪個衙門的大人,柳乘風反問他:“你說呢?”
這車伕笑道:“大人要去煙花衚衕百戶所嗎?哦,小人知道了,大人文質彬彬,又從宮裡出來,想必是新進的翰林,這煙花衚衕是非多,想必大人是要微服私訪的。”
柳乘風不笑了,心裡說,原來我是新進的翰林,這倒是有趣。
那車伕問柳乘風到底是不是。
柳乘風只是不答,車伕便洋洋自得的道:“想必是被小人言中了,呵呵……”他爽朗笑了笑,頗爲自得。
這一路到了煙花衚衕百戶所,柳乘風從車中下來,那車伕剛要說一句:“大人小心……”那煙花衚衕百戶所門口的幾個校尉正帶刀衛戍,自從柳乘風押去了大理寺,煙花衚衕百戶所這邊,已經漸漸沒了多生氣,雖然王書吏還在勉勵維持,可是沒了柳百戶,這裡頭的變故已經越發明顯了。
柳百戶在的時候,大家行在街上都是橫著走,煙花衚衕的油水,也無人敢來足,只是柳百戶一走,不只是東廠來了人,連那順天府也一下子冒了出來,煙花衚衕的油水,已是驟減,越發不如從前了。
這時候門口的校尉見到柳乘風從馬車上下來,都以爲自己看錯了,隨即眼睛,確認是柳乘風之後,立即大喜過,從前還不覺得這百戶大人的好,可是一旦離了他,才知道沒有百戶大人不要說吃香喝辣,連西北風都眼看沒得吃了,再加上素來對柳乘風的敬重,這幾個校尉竟是眼眶都有些紅了,忙不迭的衝上去,紛紛拜倒行禮:“百戶大人,您可回來了?”
Advertisement
“大人,無事就好,無事就好。”
柳乘風不了他們的熱切,剛要說有什麼話進裡頭說,我先付過了車錢。可是他一轉手,那馬車就了,車伕竟是臉蒼白,二話不說的揚鞭馬,飛快要走。
柳乘風不大:“喂,車錢!”
他是個死心眼的人,坐了你的車,車錢就非給不可,眼看馬車要走,便連忙追上去,可惜還是遲了幾步,只得力追趕。
那幾個校尉見了,先是一頭霧水,隨即有人醒悟:“還愣著做什麼,把那賊骨頭的車伕攔住。”
幾個校尉隨著柳乘風一道兒追。
車伕在前頭瘋狂趕車,看到後頭的人要追上來,更是嚇了一跳,練練催促馬兒快跑,只是這裡畢竟是繁鬧的街市,很是擁,車伕不得已,只好拉住繮繩,希律律的停了車,若是再慢一刻,前頭一個擺在路邊的攤子和三四個閒人,只怕就要撞到了。
猜你喜歡
-
連載1884 章

帶著軍火庫到大明
秦牧穿了,帶著二戰軍火庫穿了!什麼?揚州被圍,陷落在即?老子有衝鋒槍!八旗騎兵滿萬不可敵?老子有重機槍!毅勇巴圖魯頭鐵?看我狙擊槍招待你!孔有德紅夷大炮厲害?看老子山炮野炮榴彈炮轟死你!倭寇趁火打劫?老子鐵甲艦登陸!看秦牧殺建奴,平流寇,滅貪官,掃倭寇,重整山河,再現華夏神威!畢竟老子有軍火庫金大腿,要當球長的男人!
341.1萬字8 45072 -
完結3129 章

上古強身術
一個帶著上古強身術和養生之道一系列輔助性的功法的人穿越到九州大陸,他是否能站在這世界的頂端,十二張美女圖代表這個世界的十二個最風華絕代的女子!
545.2萬字8 248855 -
完結770 章
重生都市之商海狂龍
他帶著滿腔虧欠重生。 攜步步先機,重登財富之巔! 誓要獨寵妻女,為其加冕無上榮耀。 奈何造化弄人,一腔愛恨,終是錯付。 從此后,龍如花海,總裁小姐,學霸校花,未出道明星甜心,一場場愛恨情仇。
146.9萬字8.18 39851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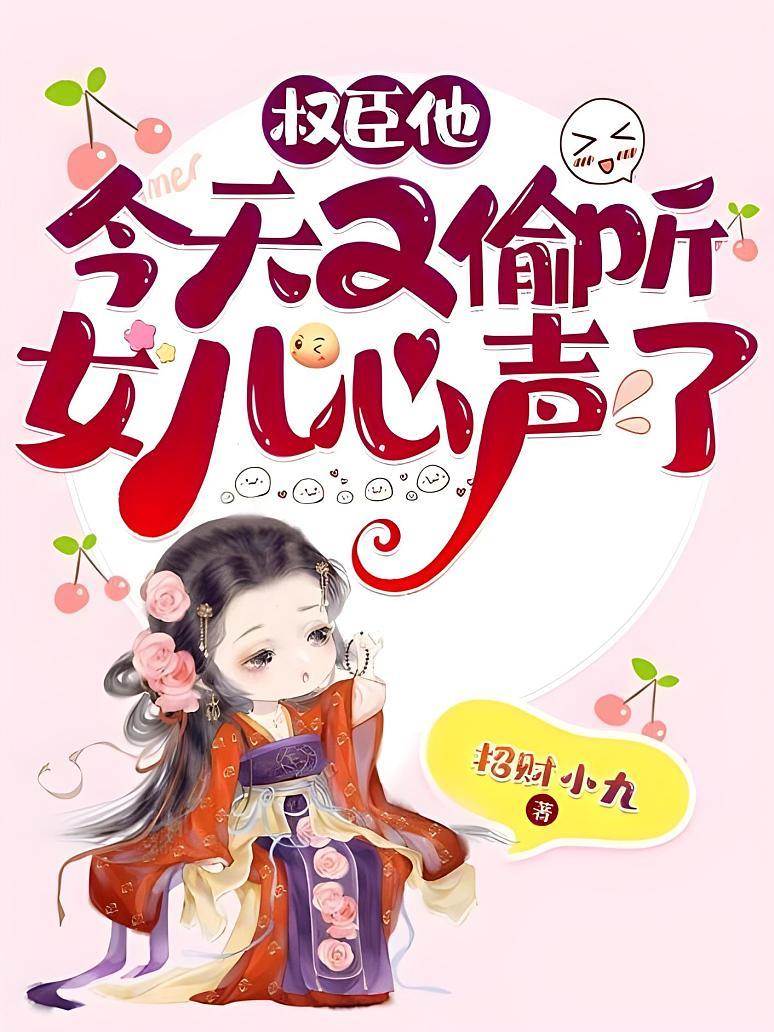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