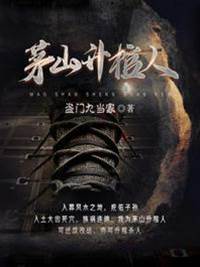《黑水屍棺》 六百二十四章 龍骨梯田
何紅湊到那扇門前看了看,轉過來對我說「有人過地窖的門!」
我也跟過去看了看,果然看到門板上的黴斑有落的痕跡,確實有人曾在不久前過它。
可這不像是劉尚昂的風格,他很小心,就算進地窖,也不會在門上留下這麼明顯的痕跡。
我將何老鬼給李壬風,隨後拉開了木門,由於木製的門板已經高度膨脹,在我拉開它的時候門軸傳來一陣非常刺耳的聲。
如果梁厚載他們真的在裡麵,是聽到這陣聲響,就應該有所行了。
可直到木門被完全開啟,地窖裡也沒有傳來任何靜。
地窖部一片漆黑,我隻能拿出手電筒,朝裡麵打了打,就看見在通向深的樓梯上散落著幾個空彈殼,那是穿甲彈的彈殼。
我頓時興起來,劉尚昂他們應該就在裡麵!
當時我也沒想太多,立即鑽了進去,可來到樓梯底部的時候,我用手電筒掃了掃隻有十幾平米的地窖,除了在牆角位置立著一個揹包,這裡一個人都沒有。
我端起手電筒,朝著揹包上打了打,那個揹包的樣式和我的一模一樣,應該是羅有方或者梁厚載留下來的,而在揹包附近,還散落著一些沒吃完的餅乾和半瓶水。
看到這些東西,我纔回想起樓梯上的彈殼落點不對頭,再次回頭看了看樓梯。
彈殼大多落在樓梯的上三節,說明劉尚昂在開槍的時候,應該是匍匐在地窖門口,他當時究竟是和什麼人火,為什麼地窖外麵沒有彈殼呢。
我跑到外麵,看了看地窖對麵的牆壁,那裡沒有彈孔。
這就怪了,劉尚昂朝對麵開槍,如果他的對手是人,為什麼要用穿甲彈?為什麼穿甲彈沒有打到對麵的牆壁?就算他槍槍命中,穿甲彈在穿人之後,一樣會飛到牆壁那邊去,而且地上也沒有跡。
Advertisement
李壬風走到地窖門口問我「怎麼了,梁哥他們不在裡麵嗎?」
我沒心思理他,又回到地窖,仔細看了看裡麵的環境。
除了那個揹包和沒吃完的食,積滿灰塵的地麵上隻有一串散的腳印,我努力分辨著,很快就辨認出梁厚載、劉尚昂、羅有方三個人的腳印,可除了他們,還有其他人來過這裡,在地麵上,還有一個不帶任何花紋的鞋底印,從形狀上看,像是千層底的老布鞋。
這時李壬風也跑了進來,問我「梁哥他們不在啊?」
「他們來過,」我蹲著子,看著地上的腳印,簡單地回應他「但不久前又離開了。」
說話的時候,我刻意讓語氣平穩,可現在我的腦子裡其實已經了一團。
梁厚載他們到底上了什麼,為什麼劉尚昂會開槍,為什麼他們要匆匆離開?
我想了很久也沒有任何頭緒,隻能暫且離開地窖,回到了地麵上。
何紅大概是看我臉不太好,問我一聲「出什麼事了?」
我搖搖頭「目前還不確定。村裡人什麼時候起床?」
「一般是早上五點鐘左右吧。」何紅回應道。
我拿出手機來看了看,在這個地方收不到訊號,好在不影響顯示時間。
現在是臨晨三點半,離村民起床還有一段時間。
收起手機,我就讓何紅帶路,說要去薑井那邊看看。
和進來的時候一樣,還是我先躥上牆頭,準備好鋼索以後,李壬風爬出院子,我們兩個再合力將何紅和何老鬼拉出來。
這一路上,何老鬼都表現得非常安靜,現在他睡著了,睡得很沉,估計一時半刻不會醒來。
何紅帶著我們走上了村子西側的一條小路,說,從這條路出去就是一段很陡的山路,過了山路,纔是農田。
Advertisement
剛開始,我以為口中的「農田」和平原上的那些田野一樣,也是大片的耕地連在一起,中間用坎道隔開,不同的地有不同的,一塊挨著一塊。
走完五六裡山路,何紅帶著我來到了一個很大的山穀中,我這才知道,口中的「田」其實是大片梯田,田間還散著堆砌著犁和一些白的亞麻袋,何紅說,每天早上村民來到這裡以後,就會用犁將地麵劃開一道道口子,將昨天播種的種子掏出來,再將麻袋裡的新種子種下去。
抬起手來,指著不遠的一座土丘對我說「龍骨梯田的頂端就是薑井了,你那些朋友真的會到這來嗎?」
其實在剛才上了山路的時候我就已經意識到,這片農田離村子太遠,劉尚昂恐怕不會特地來這裡檢視。
但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我還是沖何紅點了點頭「先看看再說,他們也許就在薑井裡。」
山穀中風聲呼嘯,何紅帶著我們來到土丘的時候,風力起了土丘上層的砂礫,我們隻能用手遮住眼睛,很艱難地朝土丘頂上攀爬。
也是走近了以後我才知道何紅為什麼稱這座土丘為「龍骨梯田」,九封山門人在土丘上挖出了一圈圈很深的壑,壑兩側的土高高隆起,就像是一條條狹長的龍骨。
李壬風看了看土丘上的,問何紅「井口就在土丘頂上嗎?」
何紅點了點頭「對啊,我剛纔不是說過了嗎?」
李壬風又問「這個土丘,是人為壘起來的吧?」
何紅依然點頭「前年六月份的時候,六長老說是要種薑,於是指揮門人壘了這麼一座土丘。」
「種什麼薑,他這是想破壞九封山的風水啊!」李壬風有些無奈地說「如果隻是這樣一座土丘還好,關鍵你們還在頂上挖了井。那個井口本就是一道生門,九封山的風水是按照八門遁甲來的,開、休、生、傷、杜、景、死、驚,八道門的位置本來是固定的,他在這裡做一道生門,你們九封山的風水局就全破了。風水一破,氣運也跟著散。難道你們九封山就沒有一個懂風水的人嗎,這麼簡單的局,但凡懂一點風水的人都能識破。」
Advertisement
何紅呆立原地,臉上是掩不住的驚愕「你是說,六長老是?對啊,為什麼駐守後山的九封山門人都被困在村子裡,唯獨沒見到他。」
我現在對九封山部的事提不起毫的興緻,手拍了拍李壬風的後背「先找人,別的事以後再說。」
說話間,我已經到了土丘的頂端,在這裡確實有一個很大的井蓋,那個井蓋上還鑄著「九封山」的字樣。
我掀開井蓋,用手電筒照了照,這口井至有五六米的深度,在井壁上鑿了很多能落腳的坑,權當是梯子了。
手電筒的束在井中晃了幾下,我沒察覺到有人進來過的跡象,心中頓時有些失落,無奈地嘆了口氣,自言自語地說「看樣子,梁厚載他們確實沒來過。」
可就在這時候,井裡突然傳來一個悉的聲音「是道哥嗎?」
這聲音我太了,不是劉尚昂還能是誰?
聽到他說話,我一直懸著的心瞬間落下來了,隨之心中又湧起一份重逢的喜悅,立即朝著井中喊「是我。你們三個都在嗎?」
井底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片刻,劉尚昂和梁厚載同時從井口正下方冒出頭來。
看到他們兩個,我就更安心了。
梁厚載仰著頭朝我喊「都在呢。不過羅有方出了點問題。道哥你快下來看看吧,他是氣,隻有你能救得了他。」
我也沒廢話,立刻下井。
這是我第一次下薑井,過去我以為,井嘛,就應該是一口氣通到底的,薑應該就是存在井口的正下方。
下來以後我才知道,豎直的井隻是一個通道,在井底,還要挖一個專門用來存放生薑的儲藏室。做法就是在靠近井底的土壁上挖出一個足夠一人穿行口,然後順著口橫挖、拓寬,掏出一個五六平米的小土。
Advertisement
我來到井底的時候,視線穿過劉尚昂和梁厚載,就看見羅有方躺在薑室的最裡麵,他上捆著一圈一圈的鋼索,子還在不停地。
梁厚載對我說「他的氣不控製了,需要氣來製衡。」
如果不是羅有方出了問題,我現在一定會分別給梁厚載和劉尚昂一個熊抱,但眼下我們都沒有這樣的心。
我疑道「羅有方不是鬼胎嗎,他怎麼還怕氣?」
「沒辦法,那氣太強了,」梁厚載說「而且它好像是直衝著羅有方來的,我和劉尚昂都沒到影響。」
我現在也沒心思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趕湊到羅有方跟前,一手頂著他的人中,另一隻手放在他的額頭上。
我不敢直接將帶有氣的念力注到他的,因為我上的氣太剛烈,就怕他會到傷害。隻能用背的手法將一小縷黑水棺的炁場凝聚在手指尖,一點一點地幫他化解氣。
他上有兩氣,一是屬於他自己的,純,但非常安靜。另外一則十分暴躁,此時正在羅有方的快速流竄著。
我小心控製著黑水棺的炁場,隻消解了那暴躁的氣。
隨著那氣漸漸消散,羅有方終於停止抖,很快,他的呼吸也變得平穩下來,但一直沒有睜開眼。
我試了試他的魂魄,雖說被那氣衝撞之後變得有些虛弱,但好在十分完整。
劉尚昂有些擔憂地問我「他沒事吧?」
我點點頭「沒事,隻是暫時昏睡,估計用不了多久就能醒過來。」
一邊說著,我手解開了羅有方上的鋼索,讓他睡得舒服一些,隨後才長出一口氣,站直了子。
李壬風也下來了,他一看到劉尚昂和梁厚載就笑了「哎呀,可算找到你們了。」
梁厚載沖李壬風禮貌地笑了笑,劉尚昂直接沒理他,在一旁問我「你們是怎麼找到這來的?」
「說來話長,」我回應他「剛才我去過祠堂那邊的地窖,見你們已經離開,才找到這來的。對了,你們在祠堂那邊遇到什麼事了?我看到臺階上還有穿甲彈的彈殼。」
猜你喜歡
-
連載59 章

茅山遺孤
一把桃木劍,一個羅盤,一把朱砂,鬥惡鬼,捉僵屍,茅山遺孤,修煉傳承道法,在走風雲江湖。
11萬字8 5942 -
完結1272 章

鎮龍棺
爺爺死的那天,萬獸拜靈,九龍抬棺......
115.8萬字8 73687 -
連載83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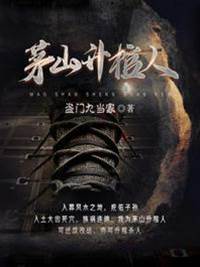
茅山升棺人
我從一出生,就被人暗中陷害,讓我母親提前分娩,更改了我的生辰八字,八字刑克父母命,父母在我出生的同一天,雙雙過世,但暗中之人還想要將我趕盡殺絕,無路可逃的我,最終成為一名茅山升棺人!升棺,乃為遷墳,人之死后,應葬于風水之地,庇佑子孫,但也有其先人葬于兇惡之地,給子孫后代帶來了無盡的災禍,從而有人升棺人這個職業。
153萬字8 952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