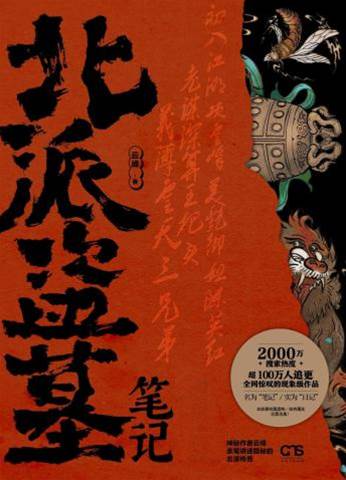《黑水屍棺》 六百六十七章 簽名簿
閆曉天點頭。
梁厚載轉過頭來對我說「這個李炳申的嫌疑確實很大,咱們把所有簽名簿都找來看看吧,看看他這兩年都在那些地方活。」
我說行啊,反正現在也沒有其他線索,就先從李炳申查起吧,不過在這之前,得先把傭兵的理了。
仉二爺讓王磊留下來理,隨後就催著閆曉天去找簽名簿。
畢竟是一條人命,對於傭兵的死,我是必須要上報給莊師兄的,但莊師兄不知道在忙什麼,電話打不通,我就讓王磊先把放在矮樓裡,閆曉天也說那座矮樓已經荒廢了很多年,平時也沒人進去,將暫存在那裡是個不錯的選擇。
閆曉天說,百烏山門人的巡邏點總共有八個,分別是藏寶閣、大殿、後穀、刑堂、鎮魂街,以及百烏山的三條大路,其中的後穀,就是世長老閉關的地方,而在鎮魂街的盡頭就是百烏山的室,前兩次來百烏山的時候我還去過那。
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一條東西走向的長街,走在路上的時候我就問閆曉天「剛纔在藏寶閣的時候,你的話沒說完,重建大殿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閆曉天說「當初重建大殿的時候,將六個唐三彩瓷瓶埋在了大殿的底基,大師父說那六個瓶子是從一個雲遊道士手裡買過來的,是六個骨瓶,骨頭的骨,價格不菲。」
我有些疑「骨瓶是什麼意思,裡麵裝著骨頭嗎?」
閆曉天「好像是瓶上進了一些骨灰,的我也不太清楚,如今在百烏山,已經沒幾個人知道大殿底下埋著骨瓶了,大師父對這些瓶子的瞭解也不多,隻知道它們埋在大殿底下。」
梁厚載說「難道說,那些人潛伏在百烏山,就是為了找這幾個瓶子?閆曉天,除了你和老夫子之外,還有誰知道骨瓶的事?」
Advertisement
閆曉天沉思片刻纔回應道「沒了吧,主要是平時也沒人提這事,我也不知道還有誰知道。」
在我們三個說話的時候,不遠又出現了幾個巡邏的百烏山門人,梁厚載立即對閆曉天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
幾個百烏山門人見到閆曉天,很恭敬地行了禮,閆曉天象徵地詢問了一下他們巡邏的況就讓他們走了。
五六分鐘之後,我們來到了位於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座老樓前,樓門上掛著一個很大木匾,上書「風水堂」三個大字。
閆曉天一到門口,立即就有一個材渾實的中年人迎了出來,他上的道袍有著墨藍的鑲邊,在百烏山的地位應該很高。
他朝著閆曉天恭敬地抱手作揖,喚一聲「掌派。」
閆曉天則禮貌地沖他笑了笑「安長老,門人簽到用的那個本子應該在你這吧?」
安長老也不廢話,立刻進了堂,又拿著一個厚厚的本子出來,將它給閆曉天。
閆曉天一邊將本子遞給梁厚載,一邊向我介紹「安長老算是我的師兄,當初趙德楷在百烏山作的時候,他還在終南山那邊閉關。」
出於禮貌,我笑著向安長老點頭,他隻是向我,沒有任何表示。
梁厚載快速翻了翻本子,沖我和閆曉天搖了搖頭「他沒在這裡當過班。」
安長老這才問了一聲「誰?」
讓我沒想到的是,閆曉天立刻回應了他的問題「李炳申。」
安長老「他隻在四個地方當班。」
閆曉天「哪四個地方。」
安長老「大殿、後穀、鎮魂街、藏寶閣。」
閆曉天頓時皺起了眉頭「這四個地方都是門人最不願意去的,他怎麼專挑這樣的地方當班呢?」
安長老「李炳申有問題。」
我們一群人全都向了安長老,隻等著他說出下文,可他的話到這裡就結束了,我們等了半天,他也沒再說什麼。
Advertisement
後來還是閆曉天問他「李炳申有什麼問題?」
安長老很簡潔地回答「人品有問題。」
我估計安長老可能在平時就是這個樣子,閆曉天也是一副很頭疼的表,又問他「李炳申的人品有什麼問題,你為什麼覺得他人品有問題,他有哪些表現,讓人認為他的品質有問題?」
閆曉天問了這麼一大串話,可安長老的回應依舊非常簡單「貪財、懶、佔小便宜。」
劉尚昂有些不耐煩了「不是,我說你能不能多說點,就這麼幾個字幾個字往外蹦,弄得人怪著急。」
我擺了擺手,示意劉尚昂別多,然後問安長老「除了貪財、懶、佔小便宜,李炳申還有別的問題嗎,他在這兩年裡,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舉。」
安長老眼睛著屋頂,好像在沉思,過來一會才對我說「我不他,沒人能得他。」
這就是安長老的回答,我心裡很費解,如果不都算是問題的話,那在他眼中,這世上有問題的人豈不是多了去了。
閆曉天對我說「安長老和我一樣,都是師從於大師父,我們都練過觀心觀耳的法,平時我沒什麼時間去接那些門弟子,當年安長老和他們接比較多,他說李炳申有問題,李炳申肯定有問題。」
我問閆曉天「你看人看得準,也是因為練了那樣的法嗎?」
閆曉天對此不置可否。
隨後閆曉天又對安長老說「這樣吧,安長老,你也別在風水堂待著了,帶上幾個室弟子,四轉一轉,咱們百烏山可能有妖混進來了。」
聽到閆曉天的話,安長老先是驚了一下,他瞪大了眼睛,好像在問閆曉天,百烏山裡怎麼會進來妖?但他終究還是沒將這個問題問出來,點了點頭就轉上了樓,我估計他應該是去集結弟子了。
Advertisement
閆曉天建議先去大殿那邊看看,我和他的想法不一樣,我打算先去鎮魂街,那裡有百烏山的室,兇神也經常過去,加上兇神的記憶被抹去,也有可能和那間室有關。
最終閆曉天還是贊同了我的提議,我們一行人離開風水堂,走過幾條小路,再次回到了老夫子常待的那座老房子。
走在路上的時候,我就發現,小路兩側那些原已荒廢的老樓現在已經住上了人,從正對大路的視窗中出一抹抹燈,但麵朝小路的窗戶則大多被堵住了。
梁厚載也發現了這個小細節,問閆曉天這樣的佈置是不是有特殊的說法。
閆曉天顯得有些無奈「是那些門弟子自己把窗戶堵上的,前段時間有流言說,麵朝小路的這些窗戶都是口,隻要有這些窗戶在,途徑小路的遊魂就會鑽進樓裡,那地方氣重,鬼進去,是要吸活人氣的。當時我正因為長老會間的糾紛焦頭爛額,等知道這事的時候,所有對著小路的窗戶全被堵上了。」
劉尚昂用手電筒照了照那些堵死的窗戶,自言自語地說「這些窗戶都被堵住了,百烏山的一條條小路,不都了視覺死角了嗎,這樣一來,潛伏在百烏山的人活起來就更方便了。」
梁厚載點了點頭,說「估計口的謠言,就是那夥人散播出去的。」
閆曉天「回頭我讓他們把釘窗的板子都撤了。」
我擺了擺手「別,就這麼堵著吧。現在咱們在明,對方在暗,咱們也不知道對方有多人,不知道他們藏得有多深,你拆了窗戶,他們說不定會搞出其他事端來。」
梁厚載贊同我的想法「道哥說得沒錯,將所有潛伏者都找出來之前,咱們最好不要做得太過,既不能打草驚蛇,又要麻痹他們。」
Advertisement
閆曉天嘆了口氣「也是。我說,你們怎麼回回想到我前頭呢,過去跟你們在一塊,我就覺得自己特傻,現在也算是和長老會鬥爭了幾年,我以為自己長了,可在你們跟前,我怎麼還是覺得自己傻呢。」
我拍了拍閆曉天的肩膀「不是你傻,是你經歷得太。你是不知道,我們這些年幾乎天天在生死邊緣上徘徊,一個不小心就是分碎骨,日子久了,就習慣於像這樣思考問題了。所以說我們這種人不適合做生意,因為很難去信任別人,對於邊的環境,也充滿了懷疑和不確信。」
閆曉天還是嘆氣,但也沒再說什麼。
我記得前兩次來的時候,位於鎮魂街盡頭的室還是一間很破舊的茅草房,可如今百烏山經歷過大規模的翻修,茅草房也變了水泥牆,那扇生滿銹的鐵門也換了。
一到室門口,我就應到了一很重的氣,梁厚載也覺到了,他指了指暗褐門板,問我「是兇神嗎?」
我點頭「應該錯不了,就是它。」
閆曉天開了門,那氣就順著門飄了出來,仉二爺不由地皺了一下眉頭,隨後撒開了渾的煞氣。
前有氣,後有煞氣,我們幾個被夾在中間,都是一副特別難的表,我和梁厚載皺著眉頭,劉尚昂則一直在他後的揹包,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舉。
我從口袋裡出幾塊守糖遞給劉尚昂「吃了。」
劉尚昂看著那些糖,猶豫了一下,可終究還是將它們含在了裡。
我們應到了兇神的存在,兇神也察覺到我們來了,他沿著牆角飄了出來,看看我,又看看仉二爺,最後問我「你會下圍棋嗎?」
我看了一眼梁厚載,梁厚載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對兇神說「我會下。」
兇神用特別疑的目看了梁厚載一會,好像想起了什麼,說一聲「和我對一局吧。」
說完,他的子就沒了牆壁,幾秒鐘之後,牆上的暗門就被開啟了。
我轉過對劉尚昂說「兇神今天沒有收起氣,你就別進去了,在這等著我們。」
劉尚昂不得離兇神遠點呢,找了張椅子坐下,朝我擺擺手「你們去吧。」
當我們進室的時候,兇神已經擺好了棋盤,他的一雙眼睛盯著棋盤,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595 章

愛恨已千年
自從盜墓之旅歸來之後,席昉變得很奇怪,他能看見很多看不見的東西,擁有了神一樣的力量。郝一墨變得能掌控水的一切,仿佛她就是水的化身。舊識的二人因為捉鬼緝魂而再次結緣,揭開了糾纏千百年的愛恨情仇...
110.4萬字8 33458 -
完結181 章

恐怖洞房夜
新婚夜,老公說要給我一個驚喜,沒想到――他卻吃了我!他說蘇家曆代只要右肩有月牙胎記的都被他吃掉了。重生到十歲那年,他一邊啃著我姑姑的手指一邊說:“養你十年,再生吃。”為了不重蹈覆轍,我仗著前世的記憶和多生的一雙鬼眼,意圖逆天改命!誰知突然冒出一個帥氣的教書先生:“不想被吃?我能幫你。”“怎麼幫?”教書先生妖嬈纏上身。
52.1萬字8 19288 -
連載170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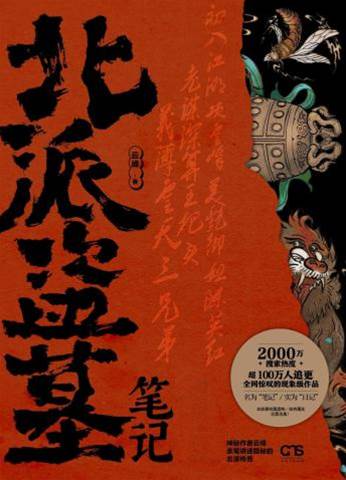
北派盜墓筆記
【盜墓+懸疑+鑒寶】我是一個東北山村的窮小子,二十世紀初,為了出人頭地,我加入了一個北方派盜墓團伙。從南到北,江湖百態,三教九流,這麼多年從少年混到了中年,酒量見長,歲月蹉跎,我曾接觸過許許多多的奇人異事,各位如有興趣,不妨搬來小板凳,聽一聽,一位盜墓賊的江湖見聞。
351.7萬字8.33 13257 -
完結957 章

驚悚降臨:這個大哥有億點猛!
陳玄北外號地藏,意外穿越到驚悚降臨的平行宇宙。陳玄北身上紋著十殿閻王,肩膀上扛著死神巨鐮:“抱歉各位,這個地盤我要了!”裂口女:“警察局嗎?有個人把我嘴縫上了!對,剪刀也給我扔了!”貞子:“城管嗎?有個人用水泥把我家井給堵死了,我回不去家了!”旱魃:“還有天理嗎?我在棺材了睡了一萬多年了,有個人把我抓出來,打了我兩個大逼個!還讓我交物業費!”自從陳玄北到來,无数厉鬼竟然变成了弱势群体!
125.5萬字8 122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