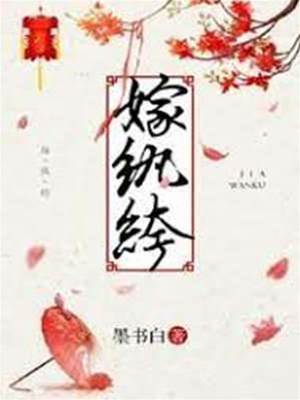《宦妃天下》 第138章 藍翎之死
“小姐,你怎麼知道,是誰告訴你的?”白嬤嬤不一震,愕然地著西涼茉。
“還需要人告訴麼,嬤嬤,這種才子佳人橫遭拆散的故事,自古以來話本里比比皆是。”西涼茉淡漠地道。
就藍翎那種天之,憑藉著點心機智謀和元帥父親的威視赫赫,贏了幾場仗,封了個將軍,便不知什麼做‘天子一怒,伏千里,流河’,一直把那個養在家中的食人虎當乖順貓兒,完全看不清什麼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但不勸誡著自己父親急流勇退,還往槍口上撞,會落得今日下場,也是理所當然的。
西涼茉的話冰冷而刺耳,讓白嬤嬤當場變了臉,失聲道:“小姐,您怎麼能這麼說夫人,當年陛下不顧夫人已經嫁爲人妻之事,強行令夫人宮侍寢,還要冊封夫人爲妃,夫人當時已經懷了你,也是爲了保住你,夫人才肯勉強侍寢,卻因此失卻了國公爺的歡心,被國公爺猜忌!”
西涼茉挑眉:“是麼,爲了保住我,那我倒是寧願不曾保住我,否則也不會讓所有人都跟著罪。”
白嬤嬤急了,咬脣道:“後來小姐出生之後,陛下仍舊不肯死心,只道你是他的骨,強要帶走你,若你不是他的骨,便要殺之,夫人無法,只能承認你是陛下骨,並對你不聞不問,同時發誓就此遁空門,不再涉足紅塵,以反抗陛下如此強佔臣妻的行徑,方纔保住了你一命,這麼多年來也是爲了這個原因,不敢對你施以半分明面上的關懷,但是奴婢也是夫人籍著靜小姐的名義被送到您邊來保護您的!”
西涼茉聞言,頓時忍不住低笑出聲。
Advertisement
“呵呵……。”
白嬤嬤又氣又傷心:“郡主,您,您怎麼能這樣,夫人爲了保護您,甚至要國公爺立誓永遠不能未經的允許踏這佛堂,當初夫人對國公爺的心,無人不知,能做出這樣的決定還不是爲了您麼!”
西涼茉笑夠了,方纔淡漠地道:“其實與其說是爲了我才做出這樣的決定,倒不如說是爲了西涼無言,我那薄的父親才做出這樣的決定,對我的父親不是一直不肯死心,所以才留在了這裡,否則大可以去外頭庵堂出家,又何必一直呆在國公府,不就是既恨我那父親拋棄誓言,一娶再娶,又不肯放棄自己正室的份麼?”
藍翎夫人以在府邸佛堂清修名義永不出佛堂一步,卻也是昭告府邸中所有人,纔是靖國公的正室,就算是韓夫人那樣出高貴的子掌了府中大權,也休想越過去。
至於西涼茉這個兒,於而言不過是帶給丈夫猜忌的孩子,就算初衷也許真是想保住這個孩子,但到了後來,經歷了漫長時間的折磨與期盼得不到迴應,丈夫不斷地娶妻納妾,讓越來越失之餘,恐怕也連帶著恨上了這個帶來丈夫背心背德的兒。
白嬤嬤聽著西涼茉涼薄而尖利的話語,臉越發的蒼白起來,卻無法做出有力的反駁。
是的,除了剛出生那一個月,夫人後來再沒有抱過小姐一次,每次召過來也是有其他事要吩咐。
但是,白嬤嬤依舊忍不住下意識地辯駁:“小姐……你……夫人不是這樣的,是真心疼你的。”
“真心疼我?”西涼茉譏諷地勾起脣角,若藍翎真的對這個不祝福的兒真有什麼母之,年過得如此悽慘,比一個下人都不如,藍翎夫人又怎麼會不知道,以白嬤嬤一人之力本無法護得西涼茉周全,否則真正的西涼茉也不會慘死,而有了自己這個‘西涼茉’出現。
Advertisement
“一個猜忌自己的妻子,薄寡義;一個天真又冷漠愚蠢,我那父親和母親果真是般配!”
西涼茉譏諷的話語剛落,忽然一個影大步走過來,對著西涼茉怒叱道:“茉丫頭,休得如此對你母親不敬,是誰教導得你如此無禮蠻的!”
西涼茉和白嬤嬤轉頭一看,竟然是不知何時出現的靖國公,正大步流星地走過來,
西涼茉暗自冷嗤,但臉上依舊是那種似笑非笑的模樣:“父親大人,您忘了,當初教養我的不一直都是您深的韓二夫人麼?”
聽到‘深’二字後,靖國公幾乎是怒不可遏,又或者說是惱怒,竟朝西涼茉揚起了手:“你這忤逆,還不住!”
西涼茉冷笑地把臉揚起來:“你打呀,就在我死去的母親面前打好了,一定很高興地看見自己的丈夫果真是個無無義的男子,這般去了也比幾十年半死不活地挨著日子強!”
靖國公聽著西涼茉的話,再看著與那已經逝去的妻子擁有著同樣麗面孔,卻一臉倔強的兒,忽然間揚起的手就再也揮不下去。
曾幾何時,他和藍翎,還有他們的兒就已經走到了這樣的地步。
“國公爺,你不能打大小姐啊,大小姐是您的親生骨,這麼多年來過得那麼辛苦,您難道就不看在已經逝去的夫人的面上對大小姐寬容一二麼?”白嬤嬤忽然‘噗通’一聲跪在靖國公的面前,淚如雨下。
西涼茉卻依舊眼中含淚地道:“嬤嬤,你不必求他,他能爲榮華富貴拋棄母親那麼多年,我這個兒又算得了什麼?”
靖國公看著如今這場景,心頭陡然生出一種無力與深深的悲哀來,他的手緩緩地放了下來,捂住自己的額頭,彷彿力不支一般,坐在了藍大夫人的牀邊低聲輕喃:“冤孽啊,冤孽……我當初就不該娶了你,藍翎,都是我害了你!”
Advertisement
“藍翎臨去之前可有什麼言?”靖國公忽然問。
白嬤嬤猶豫了一下,才輕聲道:“夫人只留下了一句話,陌上花開,妾去矣,君當顧憐兒弱。”
西涼茉看著面前的中年男人試圖手去藍大夫人青白的臉孔,卻又不敢去,最終痛苦地以手抱頭,素來冷峻的臉上出極度痛苦的神來,一行清淚順著他的臉頰緩緩淌落。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
西涼茉並不懷疑靖國公的痛苦與難,若是當年他不曾與藍翎夫人有那麼一段刻骨銘心事,或許今日也不會這般恨滿懷。
他太過明世故,又太過執著天真。
明世故與執著天真,永不能相容。
尤其是當初靖國公對藍翎許是真心真意的,他甚至願意與藍翎夫人親,面對來自各方的力,但是他沒有想過這份意所帶來的後果會如此嚴重,在面對阻力的時候,他退卻了,猜忌了,甚至也許曾經還後悔過。
但是藍翎夫人已經拋卻了一切,又怎麼能容得他後悔?
只是一切都已經過去,已經回不去,他也不能回頭。
但藍翎夫人臨死去卻還記得有這麼一個兒,亦算難得。
只見靖國公在藍翎夫人的牀前忽然跪下,凝視著牀上的人,握住了慘白無力的手腕,輕聲道:“翎兒,你且放心,我一定會完你的願,照顧好我們的兒的。”
昏暗的屋子裡,西涼茉垂下頭,彷彿不勝悲慼,方纔那一場表演,勾起了靖國公的怒氣,再以哀怒之態,激起國公爺心底深最痛苦歉疚的緒,如今白嬤嬤這一句話,更是錦上添花,靖國公從此往後大約都會對徹底放下了戒備了,只剩下憐憫關。
Advertisement
許久之後,靖國公收拾了緒,安地拍拍西涼茉的手,喑啞著嗓音道:“丫頭,你先出去,爲父與你母親還有些己話要說,十多年了,總不願意聽我說,在不說,恐怕以後都更聽不到了。”
西涼茉聞言,以袖拭淚,哀婉地道:“父親節哀,兒先回宮了,今兒是悄悄出來的,已經是犯了宮了。”
靖國公聞言,有些詫異地看了西涼茉一眼,只以爲是來見母親最後一面的,便道:“丫頭,不必憂心,想必陛下他……。”
靖國公頓了頓:“想必他不會怪罪的。”
人死如燈滅,他們這些人此刻,怎會還有心思去計較這些。
西涼茉點點頭,行了禮,轉離開後,卻彷彿想起了些什麼,看向靖國公道:“是了,父親,母親要把什麼東西給兒,說是父親那裡才能得到圓滿,不知是什麼東西,這是母親的願,茉兒自然是想要親手完的。”
靖國公一愣,猛然擡起頭看著西涼茉,眼底掠過一:“是麼,改日你拿來看看!”
西涼茉頓了頓,道:“好。”
靖國公聽得答應,臉上出一種似喜非喜,似悲非悲的神來,隨後彷彿瞬間蒼老了幾十歲一般,對著西涼茉揮揮手:“好了,你先回去吧,這事,改日爲父會讓人通知你的。”
西涼茉點點頭,方纔轉離開。
西涼茉站在院子裡,低頭看著地上樹葉柳枝的綽綽疏影,出一奇異又冰冷的笑來。
那半塊令牌果真在靖國公那裡,早前的時候,在昏睡的時間裡也有間斷的清醒,偶爾聽見百里青與連公公說及令牌有兩塊之事原來不是做夢,而是真的。
既然百里青已經得到了其中一塊,那麼還剩下的那一塊,據之前的蛛馬跡來推測就在靖國公這裡。
雖然尚且不知這令牌有什麼用,但是若能得到手,再研究不遲。
白嬤嬤看著西涼茉的模樣,忽然心中生出一種極度的無力與悲哀來。
大小姐,已經不是當初那個純真善良的大小姐了,的心已經被夫人、國公爺,這府邸裡的所有人都迫比石頭還要堅冷漠了,本不會爲自己母親的死亡哭泣和悲傷。
“是了,嬤嬤,我那母親這般大費周章地做了這些事,是不是希我替完什麼願?”西涼茉忽然開口。
白嬤嬤一愣,有些不自在地道:“大小姐,您說什麼呢,夫人只是希最後見你一眼而已。”
“是麼?那就算了。”西涼茉也沒有再問,只是輕彎起脣角,轉便走。
白嬤嬤看著西涼茉遠去的背影,不由大急:“大小姐,難道你就不想爲夫人報仇麼?”
西涼茉頓住腳步,忽然回過頭冷冷地看著白嬤嬤一笑:“我爲什麼要爲那個蠢人報仇,自作孽不可活罷了。”
就知道藍翎那人平日裡本很把心思放在上,如今這般死後卻忽然讓白嬤嬤將所能說的事都說一遍,又做出那種彷彿一切都是爲了兒的模樣,必定是有所求。
報仇?
爲什麼要幫藍翎夫人報仇,真是可笑。
西涼茉說完,也不去理會白嬤嬤慘白的臉,轉便喚了白玉幾個準備跟著走。
臨走前,淡淡地吩咐白嬤嬤:“嬤嬤,我先回宮了,若是你記得跟著的人,護著的人,你的小主子是我,那麼茉兒永遠都會奉嬤嬤如同義母,若是您一直覺得自己是藍翎夫人的忠僕,那麼您自管去咱們名下的帳房支領兩千兩銀子並一個胭脂鋪頭,養老度日,茉兒也會爲您養老送終。”
雖然重視邊之人,卻並不表示能夠容忍有了二心,或者迫做不該做之事的邊人。
看著西涼茉頭也不回離開的傲然背影,白嬤嬤忽然黯然落淚,這是小姐在警告,不要再以夫人的意志爲命,也不要爲夫人報仇麼?
夫人,難道你已經知道了大小姐會變如今這種冷,冷心的模樣,方纔讓我尋了機會給服下忘川水麼?
可是……可是……
又怎麼能看見自己當作兒一般疼長大的,爲爲夫人復仇的利劍,爲男子的玩,一個九千歲就已經夠了。
白嬤嬤心中極爲複雜,難以抉擇,喃喃自語地流著淚。
幾乎不曾注意到一道人影不知何時從牆上翻過,走進了藍翎夫人的房間。
靖國公正握住藍翎夫人的手,輕聲低語,回憶著過往,一時哭,一時笑,彷彿抑多年的緒都在這一刻釋放。
卻忽然聽見後有所靜,他驀然回頭見著了對方,忽然冷道:“你來這裡做什麼?”
那瘦長矍鑠的人影卻冷笑起來:“怎麼,你能來,我就不能來送一程麼?”
“若不是你,藍翎又怎麼會死,陸紫銘!”靖國公眼底閃過一濃烈恨意,梭然從腰上出劍來指著對方。
來人赫然正是朝中文之首的陸相爺。
他冷漠蒼白的臉上帶著一種奇異的譏諷的神:“怎麼,賊喊抓賊,若不是你那兒對皇后娘娘手,又何至於此,別以爲我不知道,你不也就是爲了那塊藍家的令牌麼!”
……
驚瀾佛堂這一夜,註定不平靜,但是西涼茉卻並不知道後來發生的事,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宮裡,一進殿門,便見著一人坐下燈火流離下,靜靜看著書。
的燭落在他線條緻的面容上,和了他雖然無雙,但向來冰冷沉的面容。
“回來了?”他聽見響,朝西涼茉微微側過臉,微微一笑,異樣的人。
------題外話------
哦~~今天更新很勤快~9000更~~求月票~~~那個新的沒那麼快放~~放了我會通知大家的,謝謝~~~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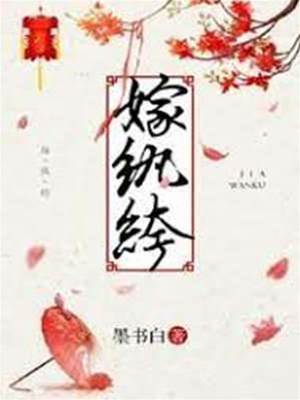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94 章

驚雀
虞錦乃靈州節度使虞家嫡女,身份尊貴,父兄疼愛,養成了個事事都要求精緻的嬌氣性子。 然而,家中一時生變,父兄征戰未歸生死未卜,繼母一改往日溫婉姿態,虞錦被逼上送往上京的聯姻花轎。 逃親途中,虞錦失足昏迷,清醒之後面對傳言中性情寡淡到女子都不敢輕易靠近的救命恩人南祁王,她思來想去,鼓起勇氣喊:「阿兄」 對上那雙寒眸,虞錦屏住呼吸,言辭懇切地胡諏道:「我頭好疼,記不得別的,只記得阿兄」 自此後,南祁王府多了個小小姐。 人在屋檐下,虞錦不得不收起往日的嬌貴做派,每日如履薄冰地單方面上演著兄妹情深。 只是演著演著,她發現沈卻好像演得比她還真。 久而久之,王府眾人驚覺,府中不像是多了個小小姐,倒像是多了個女主子。 後來,虞家父子凱旋。 虞錦聽到消息,收拾包袱欲悄聲離開。 就見候在牆側的男人淡淡道:「你想去哪兒」 虞錦嚇得崴了腳:「噢,看、看風景……」 沈卻將人抱進屋裡,俯身握住她的腳踝欲查看傷勢,虞錦連忙拒絕。 沈卻一本正經地輕飄飄說:「躲什麼,我不是你哥哥嗎」 虞錦:……TvT小劇場——節度使大人心痛不已,本以為自己那嬌滴滴的女兒必定過得凄慘無比,於是連夜快馬加鞭趕到南祁王府,卻見虞錦言行舉止間的那股子貴女做派,比之以往還要矯情。 面對節度使大人的滿臉驚疑,沈卻淡定道:「無妨,姑娘家,沒那麼多規矩」 虞父:?自幼被立了無數規矩的小外甥女:???人間不值得。 -前世今生-我一定很愛她,在那些我忘記的歲月里。 閱讀指南:*前世今生,非重生。 *人設不完美,介意慎入。 立意:初心不改,黎明總在黑夜后。
21.3萬字7.83 21942 -
完結866 章

神醫魔后
21世紀玄脈傳人,一朝穿越,成了北齊國一品將軍府四小姐夜溫言。 父親枉死,母親下堂,老夫人翻臉無情落井下石,二叔二嬸手段用盡殺人滅口。 三姐搶她夫君,辱她爲妾。堂堂夜家的魔女,北齊第一美人,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個笑話。 她穿越而來,重活一世,笑話也要變成神話。飛花爲引,美強慘颯呼風喚雨! 魔醫現世,白骨生肉起死回生!終於,人人皆知夜家四小姐踏骨歸來,容貌傾國,卻也心狠手辣,世人避之不及。 卻偏有一人毫無畏懼逆流而上!夜溫言:你到底是個什麼性格?爲何人人都怕我,你卻非要纏着我? 師離淵:本尊心性天下皆知,沒人招惹我,怎麼都行,即便殺人放火也與我無關。 可誰若招惹了我,那我必須刨他家祖墳!
228.2萬字8 394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