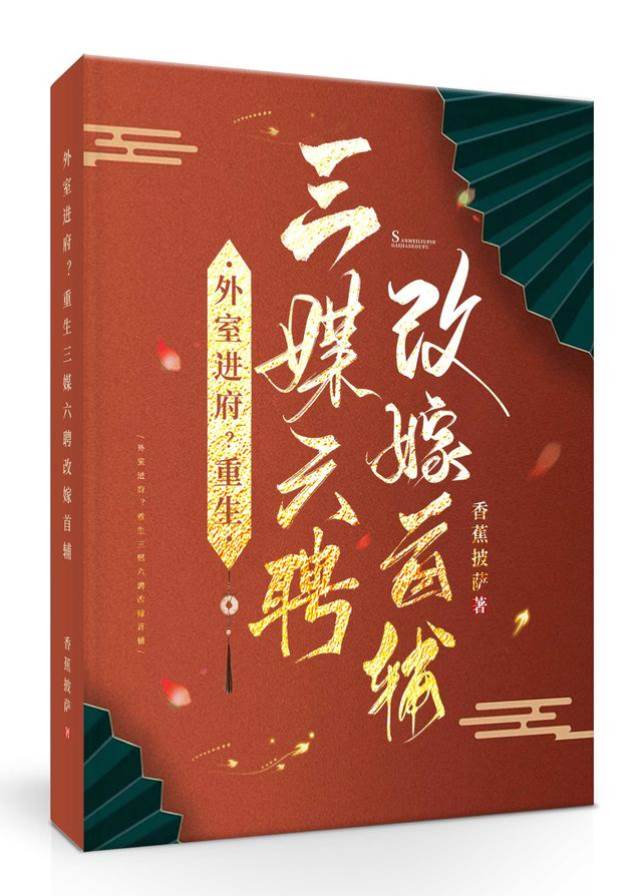《宦妃天下》 宦妻第八章
何況這個小六子還是個花叢老手。
這也是爲什麼西涼茉今兒見了這回事,要藉機發作的原因。
魅六本並不壞,其實就是個玩的大孩子,雖然看似遊戲人間的老手,但是長期刀口的生涯卻讓他不敢輕易放下心與希,但卻下意識地追尋著能讓他安枕的溫暖與棲息之,所以那麼多丫頭裡,他偏偏看上了白玉。
而白玉則是沉穩有餘,活潑不足,對男之本就不敢寄予期,也就是魅六這般連哄帶騙的從‘弟弟’做起,方纔能卸下白玉的心房,這兩人在一起本就是絕配,只不該如此這般相,否則遲早有一日會兩心傷,西涼茉今日挑破了一切的矛盾,就是希他們兩個能真的面對自己的心結。
看著魅六的模樣,西涼茉脣角勾起一淡漠的笑來:“天作孽又可爲,自作孽不可活,你且用你那張騙盡天下人臉的繼續去騙回呢。”
“郡主,您今兒做了這麼一場大戲,不就是爲了教訓小六子麼,小六子真的知道錯了!”年垮下一張秀的臉蛋,哀求地看著西涼茉。
西涼茉挑了挑眉:“你倒是聰明,只是本郡主這會子要進宮了,你如此聰明,就自己想法子挽回你未來媳婦兒和孩子孃的心罷了。”
說罷,趕蒼蠅似地擺擺手,轉也進了自己的屋換衫,徒留一臉慘然的魅六。
百里青瞥了他一眼,目惻惻地冷哼了一聲,轉也跟著西涼茉進了房。
西涼茉信賴的幾個丫頭現在都傷的傷,病的病,西涼茉也沒打算再往自己的屋子裡添人,便自己換起了衫。
百里青站在西洋雕花水銀鏡邊看著西涼茉坐在鏡子前梳頭和換宮裝,似笑非笑地道:“你對你的丫頭倒是真上心,只是不知你何時也對夫君我如此上心。”
Advertisement
西涼茉因爲解決了白玉的事,現在心不錯,換好了衫,笑著將一隻綠雪含芳的碧玉髮簪給百里青,示意他幫自己上,一邊笑道:“怎麼,難道我對夫君不是一向都非常上心的麼?”
百里青順手幫好了髮簪,低頭在雪白的耳朵上邪魅地咬了一口:“爲夫比等著看你在夜裡對爲夫上心的樣子。”
西涼茉雪白的臉頰上飛起淡淡紅霞,沒好氣地唾了他一口:“行了,我進宮了。”
——老子是阿九領著小白出來打劫月票的分界線,不給月票,就要給大部!——
夏日的夜如黑絨一般的天幕間掛著一玉盤似的冷月,夏夜長風瑟瑟地吹過深深宮,卻吹不走無邊的寂寞與憂傷。
“側聽宮說,知君寵尚存。未能開笑頰,先換愁魂。寶鏡窺妝影,紅衫裛淚痕。昭今再,寧敢恨長門。”
寂寥琴聲與子如泣如訴的幽幽歌聲飄在空曠的亭臺之上,仿若一縷芳魂的長久以來悲傷徘徊在深深的華宮巷間。
聽得人不勝唏噓。
一名提著燈籠的小宮聽得忍不住嘆:“這是哪位娘娘,好可憐呢。”
在前頭領路的大宮沒好氣地一把拉住低聲呵斥:“哪裡來的那麼多廢話,還不快走,那位娘娘也是你能議論的不要命了麼。”
小宮一聽,傻了一會子,忽然想起什麼來,下意識地道:“只有皇后娘娘在長門宮裡琴的時候不許人在周圍伺候,莫非……。”
大宮氣急敗壞地瞪了一眼,小宮趕捂住,左右看看,立刻低頭乖乖地跟著大宮一路離開。
但是,有人害怕,自然也是有人不怕的。
Advertisement
“娘娘,夜深了,一個人,不害怕麼?”男子悅耳的聲音在長門宮院子裡的假山亭裡忽然響起,令正在彈琴的陸皇后陡然停住了撥琴的指尖,臉上帶著怒地回頭斥道:“不是說了,本宮彈琴時候出現的人都……。”
但是,陸皇后的怒氣在看見來人之後,瞬間如泥牛海一般消融了。
“是你啊,小方子。”路皇后對著不知站在自己後的年青太監淡淡地點點頭,隨後又轉過臉去道:“不是說了讓你以後不要在這個時候來見本宮麼?”
小方子微微一笑:“娘娘,您看,月正好,都說對飲三人,既然這裡又沒有其他人,咱們爲何不賞月飲酒,也好過獨自一人在月下傷懷,畢竟不管自己如何傷懷,自己在乎的人都看不見。”
小方子的話讓陸皇后頓時楞了楞,隨後低頭苦笑起來:“是啊,對方都看不見,最終不過也是自己爲難自己罷了。”
說罷,擱下琴,對著小方子道:“既然帶了酒,便過來本宮這裡坐吧。”
小方子應聲過來,坐在面前,開始將自己手中的好酒、水果都一一擺上。
陸皇后看著面前的年青太監,他有著一張極爲俊的臉,材頎長,行舉止都很是風流優雅,即使面對則這個皇后,談吐之間也是不卑不。
早些日子,一直心很是不好,夜裡靠著在假山亭臺上彈琴的時候,差點從假山上滾落下去,還是路過的小方子捨命救了,所以對於小方子雖然沒有像尋常太監那般對要麼滿是敬畏害怕,要麼就是前倨後恭的態度,也能稍微容忍,何況小方子天文地理,無所不知,學識淵博,據說若非當時家中犯事,他也不會被送進宮來。
Advertisement
在這些時日裡相的日子中,陸皇后也漸漸覺得和他相起來沒有什麼負擔,倒是最放鬆的時候。
雖然說著不願意在這種時候讓人窺破心中的苦與寂寞,但是陸皇后還是有些期盼著有人能安靜地陪伴,替解解悶,訴訴苦。
只是小方子雖然在造府當差,卻是當的外差,要時常外出,並不能時常陪伴。
小方子給陸皇后倒了一杯酒,微笑著給敬酒:“娘娘,一醉解千愁,小方子敬你。”
陸皇后接過來,猶豫了一會子,便喝了下去。
小方子微微一笑,狹長的眸子裡閃過一魅,隨後又在陸皇后的杯子裡繼續倒酒:“娘娘,這酒是小方子從廚那裡來的,做兒醉,娘娘可想知道這裡頭有什麼故事麼?”
陸皇后又喝了一杯,頗有些興致地笑道:“你這個猴兒一樣的,肚子裡滿是各種故事,倒是說說看……。”
兩人便一邊喝酒一邊說笑,轉眼間,便已經是深夜了。
喝到了最後,陸皇后半醉了,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看著天邊的明月,忽然流下淚來,滄然道:“人說月圓人團圓,千里共嬋娟,今兒月圓之夜,他也不知道陪在那個小蹄子的旁邊,這麼多年,我對他難道不夠盡心盡力麼,爲何……爲何總也比不過藍翎那賤人,爲何……早知如此,當初我便不該嫁做帝王妻!”
皇后一個踉蹌,忽然向後跌去,但意料中的疼痛卻沒有傳來,一個寬闊的膛忽然攬住了,小方子溫存的帶著酒香的呼吸噴在的耳邊,激起子一種莫名的戰慄:“娘娘,何必爲了不能解你心意的人這般難過,總有人願意陪在你邊的。”
皇后了,方纔發現小方子的手在了的口的隆起之上,臉頰上微微一紅,惱地叱責:“放肆,你……好大膽!”
但是這樣的呵斥,在小方子耳中卻彷彿嗔一般,沒有任何力道。
小方子五指著皇后的臉,令轉過臉,邪肆一笑:“這才放肆和大膽。”說罷,他忽然一低頭,吻上了皇后的脣。
陸皇后徹底怔住了,但是不知是酒喝多了醉了神智,還是男人的氣息太過人,只覺得自己手腳發,裡的熱像水一般不斷地涌來,將的理智徹底地拖進了慾水的深淵之中。
猜你喜歡
-
連載1900 章

嫡女驚華
鳳驚華前世錯信渣男賤女,害的外祖滿門被殺,她生產之際被斬斷四肢,折磨致死!含恨而終,浴血重生,她是自黃泉爬出的惡鬼,要將前世所有害她之人拖入地獄!
194.9萬字8.18 337396 -
連載162 章

東宮美人
宋懷宴是東宮太子,品行如玉,郎艷獨絕,乃是世人口中宛若謫仙般的存在。南殊是東宮里最低下的宮女。她遮住身段,掩蓋容貌,卑微的猶如墻角下的殘雪,無人在意。誰也未曾想到,太子殿下的恩寵會落在她身上。冊封那日,南殊一襲素裙緩緩上前,滿屋子的人都帶著…
51.2萬字8 8875 -
完結919 章
娘子很剽悍
前世她不甘寂寞違抗父命丟下婚約與那人私奔,本以為可以過上吃飽穿暖的幸福生活那知沒兩年天下大亂,為了一口吃的她被那人賣給了土匪。重生后為了能待在山窩窩里過這一生,她捋起袖子拳打勾引她男人的情敵,坐斗見不得她好的婆婆,可這個她打架他遞棍,她斗婆婆他端茶的男人是怎回事?這是不嫌事大啊!
85.9萬字8 2980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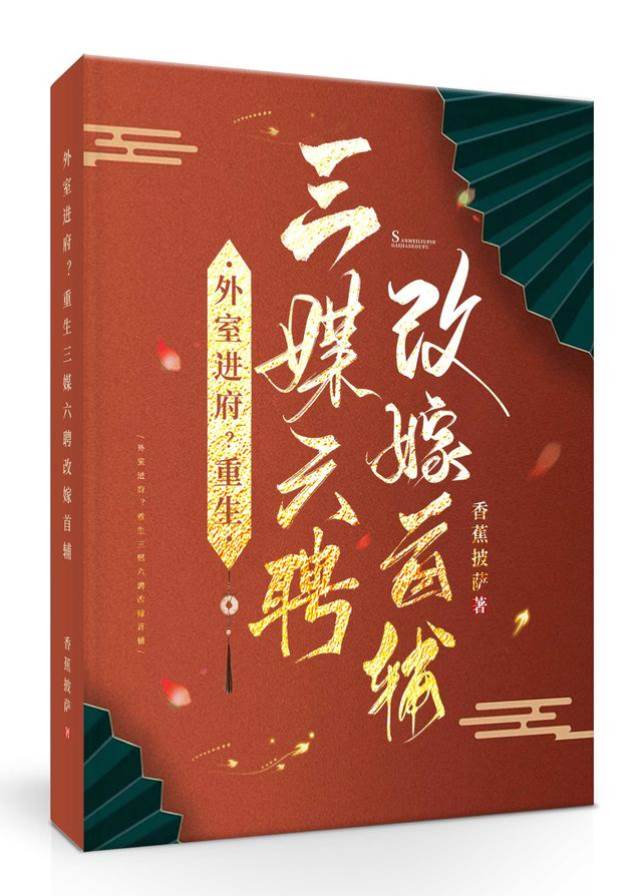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08 53539 -
完結239 章

寵妾滅妻奪嫁妝?廢你滿府嫁皇家
前世,謝錦雲管理後宅,悉心教養庶子庶女,保住侯府滿門榮華。最後卻落得一杯毒酒,和遺臭萬年的惡毒後母的名聲。死後,她那不近女色的夫君,風光迎娶新人。大婚之日,他更是一臉深情望着新人道:“嬌兒,我終於將孩子們真正的母親娶回來了,侯府只有你配當這個女主人。”謝錦雲看到這裏,一陣昏厥。再次醒來,重回前世。這一次,她徹底擺爛,不再教養狼心狗肺之人。逆子逆女們若敢惹她,她當場打斷他們的腿!狗男女還想吸血,風風光光一輩子?做夢!只是,她本打算做個惡婦,一輩子在侯府作威作福。沒想到,當朝太子莫名伸手,先讓她成爲了下堂婦,後又欽點她爲太子妃?她還沒恍過神呢,發現一直仇恨她的庶子庶女們,一個個直呼後悔,說她纔是親孃。昔日瞧不起她的夫看,更是跪在她面前,求她再給一次機會?
44.2萬字8.18 36260 -
完結185 章

小娘,你也不想王府絕後吧
西南王季燁出殯那天,失蹤三年的長子季寒舟回來了。爭名,奪利,掌權,一氣嗬成。人人都說,季寒舟是回來繼承西南王府的,隻有雲姝知道,他是回來複仇的。他是無間地獄回來的惡鬼,而雲姝就是那個背叛他,推他下地獄的人。她欠他命,欠他情,還欠他愛。靈堂裏,雲姝被逼至絕境,男人聲音帶著刻骨的仇恨與癲狂“雲姝,別來無恙。”“我回來了,回來繼承父王的一切,權勢,地位,財富……”“當然也包括你,我的小娘。”
27.5萬字8.33 87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