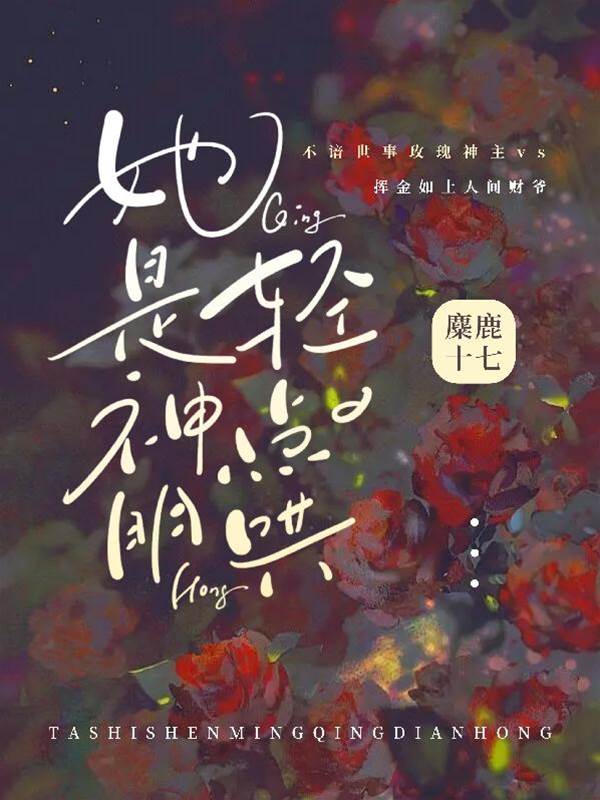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剩嫁不晚:獵愛小鮮肉》 第十七章 狐朋狗友
方錦程開車離開軍區大院直奔市中心而去,雖然已經錯過了晚高峰的時間,但在市區仍然是人滿為患,將車速從80降到了60,又降到20,當他徹底止步在一隊擁堵大軍的後頭時,已經有些想要棄車而逃了。
降下車窗,他的手指不耐煩的在方向盤上點來點去。明明擁堵的厲害,但卻仍然有從各大地下停車場開出來的私家車源源不斷的加塞進來。
華燈初上的夜,高樓大廈盡是璀璨浮華,唯獨這條閃爍著車燈的市區公路上此起彼伏的喇叭聲嘈雜的讓人想吐。
手機震起來,他隨手按了擴音。
“方!我說方,嘛呢?咋回事啊!都等你呢!來不來了啊!你坐月子呢?”
“滾!你都TM滿月了,我坐什麼月子!”
“哈哈哈!”對麵的人笑聲刺耳:“我說你不會是堵上了吧?讓你早點出門早點出門,我說什麼來著!人在市區漂!哪能不堵車,我估著你非得堵到十點!”
“你丫的烏會不會說話?我要真堵到十點,你們今晚也甭指老子買單了。”
“別介啊,這可不行啊,今晚可到你了,你要是不來,我就打軍子他爸的市長熱線投訴你!”
Advertisement
雖然看上去都是一群烏合之眾,可烏合之眾也分三六九等,和那些本質上的混混不同,能出現在方錦程邊的狐朋狗友,哪個不是這A市的太子爺?往上數三輩,隨便拎出來,那都是舉足輕重的大人。
“換地兒!我在中央路,你們過來會和,就這樣!”
“哎哎哎!”對麵話音未落方錦程就結束通話了電話。
遇到堵車已經給他堵一肚子氣了,還要被他們奚落?沒門,當然,路也沒有。
探出車窗看了看,鎖定了一條通往地下停車場的道,他現在就等著這車隊螞蟻搬家一樣移到路口了。
等待的焦灼無法言表,明明隻過了五分鐘卻好像過了五個小時一般漫長。這跑車快是快,就是可恨安軲轆不如安翅膀實在,改天問問老姐,能不能送他一架直升機,那也夠拉風的。
終於挪到停車場的口時,一輛車正從停車場駛出來,見針想要匯車流。
他額頭青筋一跳,並不打算錯過這個機會,方向盤一打,腳下油門猛的一踩,但聽一聲刺耳的吱啦聲,整個車左邊的胎沒有著地,直接著那輛車急出去。
Advertisement
又吱——的一聲在停車場的收費穩穩停下,隻有車震了一震。
私家車的車主反應過來後第一時間跑下車要罵娘,結果並未在車上找到刮痕,再看看那輛風的法拉利,以及從裡麵探頭出來的帥氣年輕人,他閉了。
方錦程不耐煩的對看呆的保安說道:“開票啊,愣著乾嘛?還想不想乾了?”
“哦哦,您稍等。”
拿了票,他這才哼著小曲發車子駛進停車場。
找了位置停好車,搭乘電梯上樓。
這樣的商場大廈在市區屢見不鮮,購,餐飲,娛樂為一,這個時間各個店麵顧客盈門。
隨手將自己所在的位置發進微信群裡,不一會就以他為圓心從四麵八方匯聚來一群所謂的狐朋狗友。
都是從小玩到大的人,在這A市之,從來不會因為找不到地方玩而發愁。
找到一家門楣裝修非常低調,但進去之後才發現別有天的酒吧,哥幾個就帶著傍家兒勾肩搭背的走了進去。
喧囂刺耳的音浪來襲,讓方錦程默默靠了一聲,這地方可比他常去的那幾家格高多了啊。
放眼看去,一個酒吧大廳就有幾百平方,用數個舞臺和吧臺隔斷,並且還劃分了不同的區域。
Advertisement
九點鐘方向舞娘正在鋼管上大秀,十二點鐘方向調酒師已經將調杯耍的妙絕倫。再看三點鐘方向,一群男正因為贏得了遊戲勝利而潑灑酒水。
更有不幽靜黑暗的角落裡,坐著些前來解但卻不願暴自己的知名人士。
剩嫁不晚:獵小鮮
猜你喜歡
-
完結1221 章

報告爹地:媽咪要逃婚
夏心妍嫁了一個躺在床上昏迷三年的男人,她的人生終極目標就是成為一個超級有錢的寡婦,然後陪著她的小不點慢慢長大成人。 「霍總,你已經醒了,可以放我走了麼?」 「誰說的,你沒聽大師說麼,你就是我這輩子的命定愛人」 一旁躥出一個小身影,「媽咪,你是不是生爸比氣了?放心,他所有的家當都在我的背包里,媽咪快帶上我去浪跡天涯吧」 男人深吸一口氣,「天賜,你的背包有多大,還能裝下爸比麼......」
193.5萬字8 13052 -
連載1504 章

夫人她A爆全世界
【甜寵,重生,虐渣,馬甲,團寵】“還逃嗎?”秦初使勁搖頭:“不逃了。”放著這麼好看的男人,她再逃可能眼睛真有病,前世,因錯信渣男賤女,身中劇毒鋃鐺入獄,自己最討厭的男人為替自己頂罪而死,秦初悔不當初,重回新婚夜,秦初緊抱前世被自己傷害的丈夫大腿,改變前世悲慘人生,成為眾人口中的滿級大佬。人前,秦初是眾人口中秦家蠢鈍如豬的丑女千金,人后,秦初是身披各種馬甲的大佬,某天,秦初馬甲被爆,全
135.4萬字8 16222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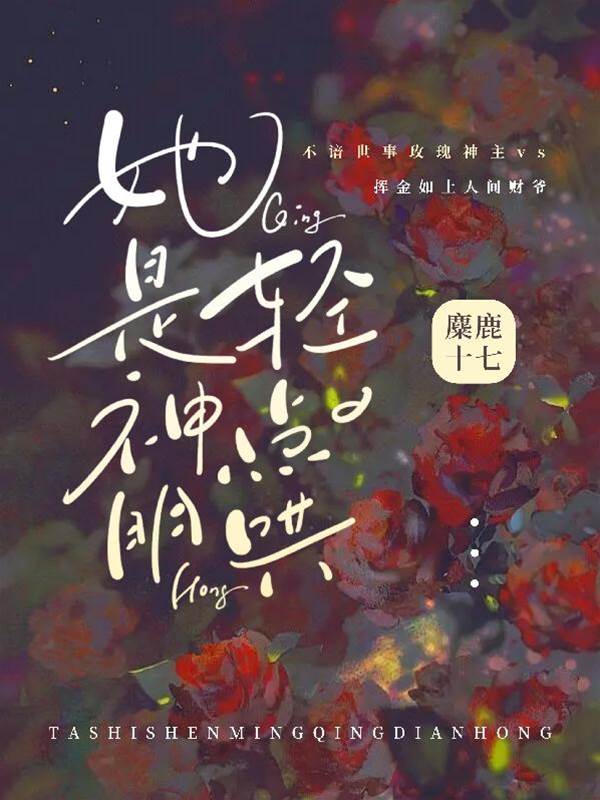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7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