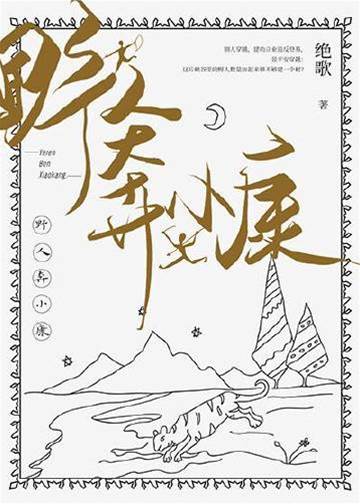《宰執天下》 第一百四十三章 梳理(十三)
“幾位哥哥,”文煌仕聲道,一繩索勒在牙關間,使得他的話變得十分模糊,“我們這是去哪兒。”
沒有人回答他。
“幾位哥哥。”文煌仕哀求道,“你們能不能放了小弟,只要你們做了,我文家一定會重重犒賞你們的。”
依然沒有聲音。
“幾位哥哥,只要你們能放了我,你們有什麼要求我都答應。”
文煌仕哀求的聲音越來越大,甚至只要有人從外面過,就能聽得見的地步。
一隻手此刻如同鐵鉗一般過來,一把卡住文煌仕的嚨。滿心要說的話,是被堵在了嚨裡。
鐵鉗般的手越收越,文煌仕兩眼翻白,兩條也不自覺地搐起來。
“記住,不要說話了。”聲音低沉沙啞,充滿了殺傷力。
文煌仕連連點頭,他真的再也不敢了。
那種窒息瀕死的覺,他昨夜躺在地上過一次。今天又是一次,文煌仕不敢再試圖去怒押送自己的賊人。
馬車不知道在道路上走了多久,一開始是走走停停,走得很慢,周圍盡是車馬的喧囂聲,但一陣嗡嗡的穿堂風過去,馬車的速度就漸漸提了上來,似乎是穿過了城門的門。
不知又走了多久,度日如年的文煌仕,終於等到了馬車的速度漸漸又慢了下來,最後停住了。
周圍沒有聲音,間或兩聲鳥,卻更加凸顯這裡的寂靜。
文煌仕子抖了起來,人跡罕至的地方,馬車押送,一連串的事實讓他想到了自己的結局。
但是立刻,一個聲音在他耳邊響起,“出去吧。算你運氣好。記住了,昨天今天你什麼都沒看到,什麼都沒聽到。如果忘了,我們隨時會回來提醒你。”
Advertisement
這是要放了自己?!
如聞佛語綸音,喜悅在心尖上炸開,文煌仕哪裡會有二話,忙不迭地點頭。被兩個人架著下了車。
厚實的頭罩被一把揭開,許久沒有到的照,文煌仕眼前一片眩。他連忙閉上眼睛,等眼中的眩稍退,才慢慢地睜開。
眼前是一片荒地,看起來足足百畝之多。後方不知,前方是一片林子,看不見人家。
這裡是哪裡?
文煌仕想著。
前面揭開他頭罩的是一個著藍的年輕人,已經退到了一邊,警惕地過來。
他不敢用太大的作,眼角的餘看見左右兩邊夾著自己的是一高一矮的男子。
後又傳來之前的聲音,“站穩了,要解你腳上的鐐銬。”
左右兩邊夾持的男子放開了手,文煌仕一陣搖晃,但立刻站穩了雙腳,等著解開腳鐐。
砰。
他只等到了一聲槍響。
得自由的喜悅凝固在了文煌仕的臉上,後腦勺在槍聲中崩碎,腦漿子濺了一地,連掙扎都沒有,撲倒在地上。
揚起的手槍,槍口還冒著嫋嫋餘煙。
開槍的男子四人中年歲最大,他小心地避開了腦漿流淌的地方,把手槍收回到腰間。
“真是可惜了。”右側個頭稍高一點的男子說著,“白投了一個好胎,要是我,早點投到都堂相公門下,憑一個‘文’字,什麼好沒有?”
“別廢話,還不幫忙把油拿下來。”矮個的男子往車上爬,呵斥著高個的男子。
“先拿鐵鍬,挖坑。”年紀最大的頭目吩咐道。
三把鐵鍬丟了下來,矮個男子自己扛了一把鐵鍬從車上跳下。
四人一起手,很快就在地上挖了一個三尺多深的長條大坑,坑中足以裝下一個人,比如倒斃在地上的文煌仕。
Advertisement
將文煌仕弄進坑中,又鏟了幾鐵鍬沾了和腦漿的土,拋進坑中,頭目回手敲了敲自己的腰背,又吩咐道,“去拿油吧。”
矮個男子回頭爬進了車廂,推出一塊長條木板來。木板一頭搭著車廂,一頭接著地面。
沿著木板,高個子在前面著,矮個子在後面扯住,小心地將一個大號的鐵桶慢慢放了下來。鐵桶用錫澆了接口和隙,市面上大桶的燈油,都是用這種鐵桶來裝。
在坑旁打開塞子,矮個男子就一腳將鐵桶踹倒。
清澈的燈油咕嘟咕嘟地從鐵桶中噴涌了出來。濺到地上的燈油開始向低窪匯聚起來,很快就浸了文煌仕的。
燈油一開始流得很快,流得多了,漸漸地就慢了下來。藍的年輕人上前去,掀起桶底,讓燈油又咕嘟咕嘟地往外噴涌。
“小心點,別弄在自己上。”頭目提醒道。
“知道了。”年輕人退後了兩步,直胳膊吃力地將桶底擡起。
燈油在坑裡越聚越多,淹沒了坑底,淹沒了文煌仕的,最後漫出了坑。年輕人乾脆用力一掀,把油桶掀到了文煌仕的上。
“差不多了。”頭目說道,“把火拿出來。”
年輕人應了,從懷裡掏出了一個火摺子。
高個矮個兩個男子從大坑旁退了兩步,看著年輕人點著了火摺子,一把丟進坑中。
火一下就躥了起來,升到一人多高,點火的年輕人沒防備,嚇了一跳。猛往後退,卻被地上的堆土給絆了一下,一屁坐倒在地上。
高個、矮個兩人哈哈大笑,年輕人大怒,回頭就罵,“笑個屁,日你孃的。”
“安生點。”頭目冷靜地說。
Advertisement
頭髮燃燒後的焦臭味飄散了出來,文煌仕的在火焰中變形扭曲。
“不會有人發現吧?”年輕人擔心地問著。
“野地裡,又沒人看著,誰能發現?”高個說道。
“還是丟進河裡安心點。”年輕人說。
“燒是一了百了,丟進河裡那更要怕被人……”
高個男子的話才說了一半。
砰!一聲巨響,一團火球在坑中炸開。
氣浪橫掃周圍,四人猝不及防,一下便被拍飛出去。
年輕人掙扎著撐起來,滿頭灰土,“怎麼,怎麼回事?”
“快跑,快跑。”高個男子一咕嚕爬起來,就往馬車那邊跑過去,“馬上就有人來了。”
被嚇到的挽馬唏律律地著,要不是用鐵銷將馬車扣在地上,馬車早就被兩匹驚馬給拖得遠走高飛了。
“還沒燒完。”年輕人道。
矮個子也站起,他捂著肚子,痛得臉發白,顯然是傷到了腑,卻強撐著往馬車走過去,道,“來不及了。”
“走!走!”頭目也爬起,大聲道。他恨恨地回頭,看著坑裡,又沒有火藥,怎麼就能炸開了?
四個人先後竄進馬車上。頭目坐上車伕的位置,皮鞭用力一揮,啪的一聲脆響,把馬車趕了起來。
一道煙塵被馬車旋轉起來的車帶起。奔馳的馬車,載著四名兇手從殺人現場飛速逃離。
……
當天稍晚一點的時候,丁兆蘭回到了府衙中。
快班廳中有總捕,還有幾名捕頭,一名老邁的捕頭正對總捕說著,“已經在文煌仕的屋子裡發現了槍油的痕跡,可以確認是新式槍支專用的槍油。”
“專用的槍油?”
丁兆蘭找了個位置坐下,就聽見一名捕頭質疑。
Advertisement
老捕頭解釋道,“之前的火槍油用的是豬油。但新式火槍不用豬油,用的是從牛裡提煉出來的黃油。”
另一名捕頭咋舌道,“連豬油和黃油的痕跡都能分清楚?”
“當然了。”老捕頭說道,“自然學會那邊派了高人來。”
沒有人再質疑證據了,只要自然學會的人做了證明,這證據就算是鐵打的。
但有人從另一個方向質疑,“誰知道這個油是什麼時候抹上去的?萬一是事後……”
“只要找到槍。”總捕打斷了質疑,說道,“現在相公們只要找到槍,別的他們可以都不在意,但那支槍,必須找到。”
“比火炮都重要?”丁兆蘭問道。
總捕很有耐心地解釋,“重要得多,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幾個捕頭換了一下報,又各自出去奔波了,只有丁兆蘭被留了下來。
“怎麼總是我被留下。”丁兆蘭屈道。
總捕沉聲說:“因爲你想做的事與他們不同。”
丁兆蘭沉默了下去,過了一下,他帶著刺地問道,“想必很快就能找到槍了。接下里會找到什麼證據?是不是直指文老太師?”
“不知道。”總捕用手抹了一把臉,有些疲累地說,“但都堂會給我們名單的。他們需要什麼證據,我們就給他們什麼證據。這就是一條好狗該做的事。”
“到最後,會抓多人?”丁兆蘭問道。
“直到都堂,不,直到兩位相公覺得安穩了爲止。”總捕擡起眼,衝著丁兆蘭笑了一笑,很難看很驚悚的笑容,“你沒想到韓相公會做這種事吧?”
自然學會背後就是韓岡,既然自然學會的人願意作證,那就代表著韓岡的意志。
“不做纔不對。”丁兆蘭幫自己的偶像解釋著,“韓相公既然明年就要離開,離開之前當然要把庭院打掃一下,免得他離開後,有人攪風攪雨。章相公當也是覺得現在不趁韓相公在,就把那些積年沉滓清理一下,等他一個人擔任相公,那再想手,他自己就要獨自承力了,哪裡有現在就做輕鬆?”
“所以你是不是打算放棄了?”總編擡眼問道。
丁兆蘭輕輕攥了拳頭,慢慢說道,“不。”
總編深吸一口氣,欣地點了點頭。卻又說,“小乙,你認識自然學會的其他人吧?”
“不是已經請過了?”丁兆蘭驚訝道。
“這裡有,府裡的老陳頭病了,他徒弟太。而且就是老陳頭還在,估計也拿不住。真的必須自然學會這方面的專家來了。”
丁兆蘭詫異地道,“請剛纔的那一位幫個忙介紹一下不行嗎?”
“方纔那個是嚴推請來的。”總捕說道。
丁兆蘭點頭,表示自己明白,就問:“什麼?哪裡來的?”
總捕道:“外城南面的一荒僻地上,圍起來準備建房,還沒有工。午後未時,突然就是一聲炸,附近的人趕過去看的時候,就看見火堆裡有這麼一焦。還有一個鐵皮油桶。賊人是用燈油燒。估計是因爲油桶中的殘油被點燃了。”
丁兆蘭皺眉沉,道:“運,運油桶,加上人,肯定是有一輛大車。車轍呢?”
“上了大路就找不到了。”
“車轍上必然有痕跡。不同的車痕跡都不同,還有馬掌。用石膏可以翻模……”丁兆蘭聲音突地一頓,驚聲道,“會是文煌仕?!”
“或許。”總捕平靜地說道。
……
“文煌仕死了?”
夜時分,韓岡在自家的書房中問道。
在他的面前,是一名面目平凡的員。這員點著頭,“死了。”
“確認了?”
“通過牙齒確認過了。”
“牙齒確認?”
韓岡覺得不對,立刻發問,“面目呢?被毀了,被燒了?”
“被燒了。被人從後腦用手槍擊殺,死後又遭焚。”那員將發現的前因後果說了一遍。
韓岡停罷,呵呵地笑了兩聲,“殺人放火,毀滅跡。”
他看起來饒有興趣地問著,“既然人都燒炭了,你們怎麼確認那就是文煌仕的?難道還有什麼證明份的地方?”
“回相公,文煌仕曾經去醫院治過牙,最裡面的智齒被拔掉了三顆。我們找到的也是一樣。除此之外,文煌仕是文家人,自吃米,看過他的牙口,的確是吃米的樣子。”
“這倒是個檢查的好辦法。”韓岡點點頭,比起千年後,這種確認辦法還是太率了,但現在已經是先進得遠遠超乎時代,“剩下的理由呢?”
“就這幾天,正好有一特徵與文煌仕一模一樣的,這機率太小了,下覺得,已經可以確定那就是文煌仕。”員一板一眼地說道,“如果相公覺得不夠,下這就去命人繼續調查。”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韓岡不耐煩地擺擺手,問,“你們打算怎麼做?”
“不明骸,給化人場理,之後送澤園。”員抿了抿,有些張眼看著韓岡,一邊說著,“文煌仕,只能從此失蹤。”
韓岡沉著,手指輕輕敲著扶手,敲得員的子一點點地繃起來。好半天,韓岡才點頭,“好吧。就這麼辦吧。”
員立刻長舒了一口氣,繃的子也鬆弛了下來。韓岡的好說話讓他徹底安心了。
韓岡觀察著員的心變化,問道:“還有呢。”
員張地搖頭,“別的下就不知道了。”
“……那就這樣吧。”韓岡想了一下,直接下了逐客令。
“下告辭。”員倒退著出了門,腳步輕快地離開,比他進來的時候,放鬆了許多。
聽著遠去的腳步,韓岡搖頭冷笑,似譏似諷,“行人司不如撤了算了,盡辦‘聰明’事。”
他從書桌邊的盒子裡出一份公函來,上面蓋著四天前的印,翻看了一下就點著了,丟進桌旁的火盆裡。
熱浪中,韓岡踱出房門,冷笑著著星漢燦爛的夜空,“真是急著讓人忘掉之前的事呢。”
……
於文守在都堂的偏門前。
在他周圍,有十來位跟他一樣的新人記者。他們被帶來打下手,沒資格進都堂裡面,近距離接掌控天下的宰輔們。
都堂今天將晚的時候通知在京的所有有名有姓的報社,說是大新聞公佈。每一家報社,都把自己的得力干將派了過來。
於文跟隨的唐梓明已經有好些時間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纔會出來。
終於,閉的側門吱呀一聲打開,一羣男子步履匆匆地衝下臺階,眼睛裡都閃著興的芒。
領頭的一人正是唐梓明,於文看見自己的前輩出來了,神一振,連忙迎上前去。
走上臺階,於文就笑著問道,“哥哥,是什麼大消息。”
唐梓明徑直往下蹦著走,肩而過時,一扯於文的胳膊,“走,走,快點走。”
被唐梓明一扯胳膊,於文就在臺階上轉了半圈,暈頭轉向地被扯著往下面走。
一大羣記者走得飛快,下了階梯後,更是將前後擺一,撒就跑,好似屁後面有老虎在追,更像是前面堆著可以隨便拿的金山。
猜你喜歡
-
完結390 章

帶著空間超市去種田
夏稻花穿越了,後腦勺上破了個大洞,誰幹的? 好消息,辛苦經營的超市跟來了! 壞消息,她住的縣城遭遇了侵略! 夏稻花在戰火中捨命救人,救出來一個帥哥,帶出來三個拖油瓶,和好幾波敵軍與刺客; 夏稻花抗旨不遵,結果竟然當上了攝政王,還被先帝託孤? 聽說夏稻花還沒嫁人,媒人踩破了門檻; 大將軍揮揮手把他們都趕走:攝政王今天不相親!
66.9萬字8 41635 -
完結548 章

穿越後,替身王爺哭著求我不和離
天下人都說,王妃葉知舟愛慘了寧王,她以一個棄妃之身,一夜之間成為神醫,治皇帝,救妃嬪,逆轉乾坤,為寧王掙萬兩黃金家財。 誰要是敢動寧王一下, 她葉知舟能提著刀把那人斬首示眾。哪怕寧王將她虐得肝腸寸斷遍體鱗傷,她也依舊甘之如飴。 直到有一日,她喝得爛醉,對寧王說: "寧渡, 你笑起來很像他,隻要你肯笑一笑, 想要什麼我都能給你。” 冷傲矜貴的寧王聞言忽然發了瘋,將她壓在床上,一遍一遍問他像誰。 後來,有人說寧王被王妃寵瘋了,王妃對他厭倦,他就跪在他門前,啞著嗓子說自己心甘情願做替身,她卻再也不肯看他一眼
82.5萬字8.33 66567 -
完結20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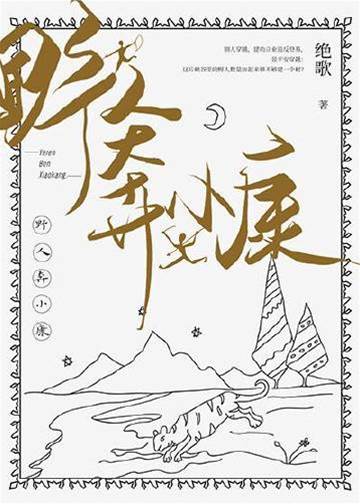
野人奔小康
景平安在職場上辛苦打拼,實現財富自由,卻猝死在慶功宴上,悲催地穿越成剛出生的小野人。有多野?山頂洞人有多野,她就有多野,野人親媽茹毛飲血。鉆木取火,從我開始。別人穿越,建功立業造反登基,景平安穿越:這片峽谷里的野人數量加起來夠不夠建一個村?…
80.8萬字8 5299 -
完結217 章

朕的愛妃太能卷了
互聯網大廠卷王姜嫻穿越了。穿越前,她剛因為焦慮癥向醫生求助:“我一天不加班渾身難受,放一天假就呼吸不暢,怎麼辦?”朋友問道:“你這病傳染不?來我公司待一下,抓緊把這病傳染開去!”穿越后,來到慢節奏的后宮,人人無所事事,她快閑瘋了!于是她二話不說,直接開卷。*某不愿透露姓名的答應:十一月份,京城雪下得最大的時候,姜答應天天在梅園跳舞!我的親娘啊,用得著這麼賣命嗎?爭寵什麼的,那就不是我們年薪四兩該操心的事。所以同年,姜答應成了美人,而她還是答應。*再后來,傳聞姜貴妃和后娘關系不睦,後孃得子後進宮求見,貴妃娘娘賞她十五字真跡,掛在便宜弟弟牀頭——距離科舉考試還有四千三百七十天。在老闆面前刷存在感,姜嫺是專業的。你見過凌晨三點的後宮嗎?宮妃五點起牀,她三點:宮妃賞花賞月看戲扯淡的時候,她在練舞練歌練琴,鑽研大老闆的喜好,業務能力和奉承阿諛兩不誤,姜閒相信,只要這麼卷下去,老闆升職加薪必然第一個想到她。而皇帝見識過無數爭寵手段。還真獨獨記住了姜嫺一一這女人實在太愛朕了!
35.6萬字8 24253 -
完結615 章

採石記
作爲穿越女的穆長寧,似乎出場就是炮灰命。 在忍不住反抗之後,老天終於給她開了扇窗,莫名其妙丟了塊石頭進來。 嗯,那就好好修仙吧……
157.3萬字8 11954 -
完結410 章
仵作狂妃
她本是令罪犯聞風喪膽的名法醫兼犯罪心理學專家,一朝穿越,成了西孰國一名普通人家百般寵愛的小女兒韓玥。 為報仇,她重新拾起解剖刀。 快速得出驗屍結果、收錄指紋的高科技人體掃描器成了她的神助攻。 為完成前世抱負,她又不得不對他百般討好。 然而,兩輩子都沒談過戀愛的她,對這種事實在是不怎麼拿手。 尤其對方還是西孰國唯一的異姓王,軍功壓人,腹黑狠辣,權傾朝野卻對女人嗤之以鼻。 初時,她笨拙地討好,做美食,送禮物。 他雙眼危險一眯:「你想從本王這裡得到什麼? “ 她鼓起勇氣:”我想借你的面子,進衙門,做仵作! “ 後來,他百般縱容,一路護航。 可惜,某女無動於衷,忍不住問道:“我這般對你,你可有什麼想法? “ 某女一臉嚴肅:「王爺放心,我會把每具屍體都驗的明明白白,絕不給你丟臉! “ 他吐血:「你敢不敢來驗驗我的心! ”
70.2萬字8.18 2174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