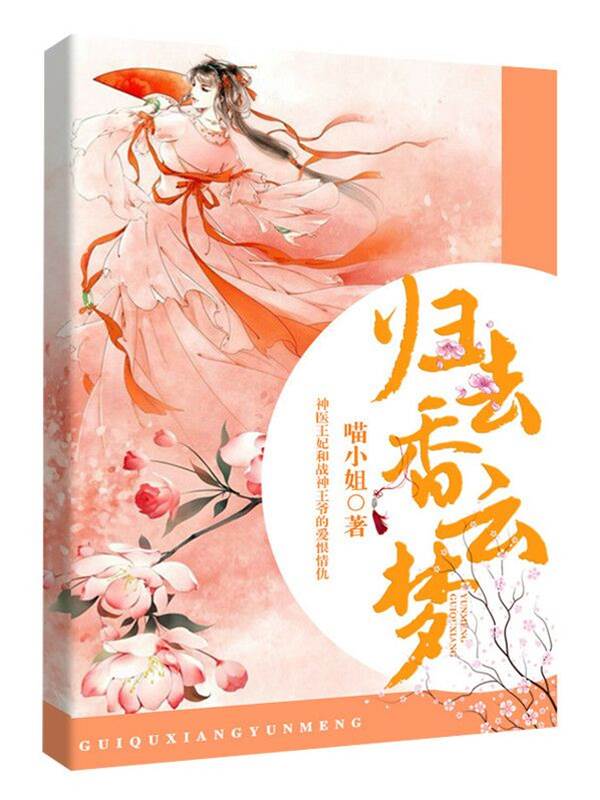《宰執天下》 第一百五十五章 梳理(二十五)
哐。
玻璃盞砸碎在牆上,葡萄酒漿染紅了半幅白牆,如同染。
趙仲惠穿過噤若寒蟬的妻妾僕婢,出門去,丟下一句話,“收拾乾淨。”
他已經三天沒敢出門,也沒敢與他的那些朋友相互流。這讓趙仲惠心中十分煩躁。即使走在自家人人稱羨的後花園中,趙仲惠的臉也是彷彿能凍住池水一般。
假山、花木與池塘融一,樓閣、畫舫、亭臺,在池水畔錯落佈置,來自大家手筆的花園,幾年前還是六戶人家共有,不過現在就只有趙仲惠一家了。他的兄弟們都搬到了新城外的敦睦宅居住。
都堂在待遇上對宗室很大方,他們在新城外,另設了敦睦宅,用來安置越來越多的宗室。
睦親宅修起已有幾十年,早就不敷使用。當一位分配了一間大宅院的宗室過世,往往就是七八個兒子將一座府邸瓜分。家家戶戶都住得的,天天爲了蒜皮的小事吵上幾架,兄弟因此反目的況很多,朝廷的臉面上很是難看。
不過敦睦宅修起之後,各家的住宿就寬鬆了許多,住得遠了,反而關係近了,兄友弟恭看起來一派和睦。
但對於都堂,趙氏宗親的反依然是一日甚過一日。都堂的舉,被他們視爲收買人心,本不需要謝。
說起來也的確如此,都堂對宗室的優待,是做給世人看的,從來沒指得到這些趙氏親族謝。
除了很一部分之外,其他宗室都憤恨於都堂將趙氏摒除於權力之外,更恐懼有朝一日謀朝篡位,趙氏地位不保,即便都堂給予他們多好,即便其中很大一部分比過去要富足許多,依然滿腹怨言。
Advertisement
故而趙仲惠纔會時常與一幫人混在一,一天到晚都在詛咒都堂早日而亡。換個說法,就是一羣敗犬在一起互傷口。
前些天,都堂前的學生鬧事,接著又當著都堂的面開了一槍,手筆讓人驚歎,一想到都堂中一衆叛逆的臉,趙仲惠就興不已。
整件事的起因經過,趙仲惠很清楚,但主使者是誰,就不那麼明瞭了。反對都堂的人數不,通常是五六人、七八人、十來人組一個小社團,就如詩社、茶會、酒會一般,社團之間往來很,只有偶爾流一下消息。
他只知道那幾天的集會中,所有人興不已,說啊說的,恨不得那些學生立刻衝擊都堂,然後被殺得流河,讓都堂失了天下士民之心。
而集會的召集者,他的一位堂叔,更是晦地說了一下這件事是有人在背後推,而且那人地位很高,一向對皇宋對天子忠心耿耿,只是因爲章韓二賊勢大,不得不暫且屈事賊。
他堂叔並沒有那人的份,趙仲惠和其餘人也都沒有去追問——如此忠貞之士萬一泄了份,有所差池,豈不是讓人扼腕終生?
想來必然是世皇恩的簪纓世家出,與那等寒酸涼薄的瘻人之子決然不同。
只是在開槍的那一天之後,趙仲惠就不敢隨便出門集會了。
讓他去罵一罵都堂可以,或者聲勢起來之後,跟著人渾水魚也行,但真要讓他出頭對抗都堂,趙仲惠還是不敢,自家命自家要珍惜。等到外間事了再行集會,這一次讓都堂灰頭土臉的事,完全可以開心的說上一年。
只是悶在家裡,先是聽說河北贏了,又聽說遼國皇帝逃竄回國,趙仲惠心裡的火就按耐不住。
Advertisement
再接著又聽說槍給找回來了,人犯的份也暴了,開封府中最有能力的爪牙已經追蹤到了開槍的義士,很快就能抓捕歸案。
趙仲惠的脾氣就像是火藥桶,只要有點火就能給了。
如果能像尋常一樣能與人一起痛罵都堂,再罵兩句耶律乙辛的無能,火氣還能消退一點,只是在家裡面,哪裡也無從發泄。
繞著池塘走了一圈,傍晚池畔清風徐徐,柳枝青翠,鳥聲婉轉,趙仲惠的心稍微好了一點。
一名僕人從匆匆而來,對趙仲惠說了幾句,趙仲惠點頭道,“讓他進來。”
一人很快被領到趙仲惠的面前,是他一位族兄家的都管,也是同一社團的同伴。
“五兄可還安好?”趙仲惠問道。
“勞郡公顧問,主人起居如常,一切安好。”都管言辭有禮地回了一句。
“你今天來,可是五兄有何吩咐?”
都管一瞥左右,上前半步小聲道,“主人命小的來報與郡公,那賊子要祭告太廟了。”
趙仲惠頓時臉孔扭曲,稍稍好轉的心登時又壞了幾倍,他咬牙切齒,“趙!世!將!憑他也配!”
都管低頭,一聲不吭。
自從之前濮王府一系被清洗之後,沒有哪位宗室還敢對趙世將就任大宗正之職有所不滿,至是不敢當中有所異論。
但是在人後,太宗皇帝的脈,自然會對太祖後裔爲大宗正而怨聲載道。
從趙仲惠姓名之中的一個仲字,就可以知道他屬於太宗一脈,與熙宗皇帝同輩——熙宗皇帝舊名仲鍼,即將登基時,才改名趙頊——對趙世將的觀可想而知。
趙世將如今奉承都堂,簡直都忘了他是趙氏子弟,這一回遼國不過是在河北兵鋒小挫,他就忙不迭要去太廟爲那羣賊子吹捧,河東慘敗不提,河北的戰事也還沒結束呢!
Advertisement
“人子的豬狗,沒臉皮的老畜生,背父忘祖的賤骨頭。”
連番污言穢語,讓人不敢相信這是來自於一位自讀書的郡公之口。
痛罵了一番,趙仲惠氣息稍平,他虎著臉問都管,“五兄還說了什麼?”
都管低頭,“主人請郡公過府一會。”
趙仲惠皺著眉,“之前不是五兄說的嗎,這兩天都不要隨便出門。”
都管道:“主人知道,所以特意安排了車子,停在後門口。只是要郡公跟平常一樣,稍改一下裝束就好了。”
“好,等吾更。”趙仲惠都沒多想,一口應承,他在家中待得煩悶,早想出門去了。
夜漸濃,換了一僕傭的裝束,趙仲惠孤一人的悄然從後門出來。門口一輛車廂低矮窄小的四小車,車廂上的油漆斑駁,澤黯淡,跟外面尋常可見的載客車看不出任何區別。連拉車的馬匹,都是用了有氣無力、髮稀疏的老馬。
“什麼時候置辦的?”趙仲惠問。比之前看到的車子,還要更不起眼。
“纔買下來的。”都管爲趙仲惠打開門,讓他上了車,然後跟了上來。
“郡公見諒。”都管側著子,在對面坐下。
前面的一聲鞭響,馬車搖搖晃晃地開始走了。
比起家裡將作監所造的馬車要顛簸了不,但趙仲惠完全能夠忍。
他現在正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跟那些同伴會合,一同宣泄這幾日在家裡悶出的鬱氣。
他甚至還在想著,等會兒集會時是不是提一下,給都堂多添添。比如趁勢煽一下東京士民,要求都堂繼續北攻遼國,攻下遼,攻下臨潢,殺契丹,看看都堂到底是做還是不做。
Advertisement
車廂中窗簾拉起,掩著車窗,看不見外面,但能聽到周圍喧囂聲漸大,顯然是進了一街市。
“好像路不對。”趙仲惠說。
都管道,“如今都中管得比之前嚴了,必須要在人多多繞兩圈,如果有人跟蹤,很容易就被甩掉。”
“小心點好。”趙仲惠點頭,繼續安靜地等待。
將都堂被民所挾不得不出兵北上,最後慘敗而歸的窘相,在腦海裡編織了三五遍之後,趙仲惠忽然發覺時間已經過去了很久,馬車繞的圈數也已經遠遠不止兩圈了。
他猛地掀開窗簾。夜幕下,周圍一片黯淡,遠能看見一個深黑的剪影,那是大圖書館的位置。
不是好像,本就不對路。
“停車!”趙仲惠厲聲道。
但完全沒人理會,馬車還在繼續向前。
“停車!”趙仲惠用力瞪著對面的都管。
都管安然坐著,臉上的謙卑換了冷冷的譏笑。
“停車!”趙仲惠又踢又撞,但車門紋不。堅固得不像是一輛製濫造、本低廉的舊車。
都管冷眼看著,帶著嘲諷,“不要踢了,都是鐵的。”
都是鐵的?!
趙仲惠的瘋狂一下停住了,他緩緩地轉過頭,看著都管,充滿怒意地吼道,“給我停車!”
“郡公,安毋躁。”都管心平氣和地說著,探出一隻手牢牢卡住趙仲惠嚨,手上傳來的巨大力道幾乎讓他閉過氣去,“馬上就到了。”
恐懼和驚訝,讓趙仲惠一時忘記了掙扎。他瞪大了雙眼,看著眼前帶著陌生表的悉面孔,在府邸中做二三十年差事的老僕,突然間就變了一副殺人放火的強賊模樣,甚至還敢對自己手,這是在做夢嗎?
他瞪著都管,馬車這時慢了下來,一座建築進窗口,那是……
史臺獄!
……
“聽到什麼了?”艾虎突然揚頭問道。
“沒有。”丁兆蘭斷然道。
寬敞的大號馬車中,開封府的名捕頭盯著對面的三人。白澤琰、智化、艾虎,之前逃離的三名人犯,現在正與他同在一輛馬車之中。
方纔只是一輛馬車相錯而過,雖然裡面穿出來的聲音有些可疑,不過那是行人司專用的馬車。外觀與市面上最爲常見的客運馬車別無二致,但丁兆蘭僅僅是分心對外一瞥,就分辨出來了。
最近的調查中,丁兆蘭對行人司在案件中扮演的角越發地懷疑起來,也找到了幾條新線索,剛剛過去的車子或許也有相應的線索。
但丁兆蘭現在的注意力都在車中其他三人上,完全沒有多餘的力去分心旁顧。
“丁捕頭,別那麼張。”智化和尚笑著,試圖安丁兆蘭,“我們可是自願自首的,不會與你爲難的。”
“是啊,是啊。”艾虎猛點著他的腦袋,又試圖去推開窗戶。
“別。”丁兆蘭盯著他,“老實點。”
智化和尚道:“丁捕頭,通融一點,車裡太悶,氣。”
“俺已經夠通融了,不拿鏈子鎖了你們,還讓你們坐車。”
艾虎道:“要真是通融,就送我們去相府。韓相公一向公正廉明,肯定不會冤枉無辜的。”
丁兆蘭冷笑:“做什麼失心瘋,真當俺是蠢人,要是讓你們去了相公府上自首,外面還不要傳說是相公指使你們的?”他冷哼著,“老老實實去府衙,只要能抓住首惡,立下功勞,自然能饒了你們的命。”
智化和尚合十唸叨:“阿彌陀佛,和尚可是冤枉的。”
“冤枉不冤枉俺不知道。”丁兆蘭瞥眼看了看上車後就一直沉默地著窗外的白澤琰,“俺只知道抓這位白公子的時候,和尚你就在旁邊……還了刀子。”
智化和尚又唸了句佛號,“和尚是被無奈。”
丁兆蘭搖頭:“俺只知道和尚你拔了刀子,其他俺可不知道。”
“你本就心知肚明。”小艾虎氣急敗壞。能一路追到白澤琰的上,怎麼可能不清楚智化和艾虎本沒有參與到槍擊案中。
丁兆蘭嘆道,“是與不是,不是俺說得算的,得讓相公和大府相信你們纔是。”
他又對白澤琰道,“白公子,你可是想好了?”
“忒多廢話。”白澤琰從窗外收回視線,“我要是不願,你能勉強得了我?”
雖然前途莫測,但已經暴了份的他,不想牽連家人,就只有設法彌補之前的過錯。
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也說不定,只要能將自己掌握的消息傳出去。
……
夜已深。
一封急報送到宿直都堂的韓岡面前。
“南康郡公趙仲惠招供了,煽士子、收買槍手這兩樁事皆他所爲,同謀的還有譙國公宗辯,榮州防使仲傑等六人。可惜他子虛弱,招供到一半就突發疾病,搶救無效,死了。”韓岡將收到的消息草略地念給章惇,然後對送信而來的信使搖頭道,“才一個時辰吧,人就這麼沒了?虧史臺也敢答應你家樞。”
信使只是呂嘉問的親隨,被安排做聯絡,聽了韓岡的話,也不知該怎麼回話,只能訥訥地站著。
別看史臺獄名氣那麼大,實際上因爲裡面關的都是人,住宿條件、飲食水平,都比京師之中一般水平的客棧都要強出許多。不說全都是單人間,鋪設牀鋪的稻草都是每日更新,只吃飯喝水,潔淨二字比外面的酒館都還要講究。
而且臺獄中審問犯,是嚴施加刑,棒皮鞭夾之類的刑一概不許使用。一旦有所違背,被曝之後,就算是宰相,也保不住臺獄中人。即使沒有加刑,只要臺獄有人犯病亡,當事的臺、獄都不了要懲。
故而獄中待人犯,總是小心謹慎,臺獄中出人命的事,幾年都難得一見。
“或許是意外。”同樣值夜的章惇代爲解釋,“這裡的趙仲惠是一個,前面的趙宗枅也是一個,招供的容都差不多,也沒說兩個都死。”他帶著玩味的笑,有幾分好奇,“之也算有能耐,一個個招供得倒是快。”
信使道:“回相公的話,就是拿勺子弄些泥漿污,在水裡飯裡攪一攪,強灌下去,就沒有不肯開口招供的。”
章惇皺眉,這種審案的方法,簡直是兒戲了,“命都要沒了,還在乎一點髒?”
韓岡倒是理解了。
在臺獄中好吃好睡,又無重刑,平添了讓人犯認罪的難度。不過住的員們,通常是認罪很快的。也沒有別的原因,只是落差二字,就讓養尊優的員無法適應,最後被熬得很快招供。
他對章惇道:“沒命要等判決後,髒東西可就在眼前了。”
韓岡不知道這是另一段歷史上,新黨曾經用來對付敵對派系的手段,不過這種手法,也只有在史臺獄中才派得上用場。換作其他監獄,上刑更加乾脆利落。
“就讓呂之就留在臺獄中了?”韓岡問章惇,“府獄還有好多空獄間,正等著人來住。”
“回頭我會跟之說的。準備流放的輕罪犯人就送到府獄去,那些犯了重罪的,還是放在臺獄吧。”
開封府的監獄,犯人流速度很快。刑案之中該殺則殺,不該殺的,或流放或小懲開釋,府獄中的犯人平均繫獄時間不會超過一個月。
因爲對犯人的置速度太快,開封府這幾年甚至還曾經還出現過兩回長達半個月和二十天的府中獄空的況。
放在過去,這是能給天子報喜的祥瑞之兆,知府也能就此打通登天之階。
但如今開封府中的犯人,最輕的上幾鞭子就放人,最重的就上菜市口,剩下的無論輕重罪,只要定罪了,基本上都是送去邊疆開荒。如此制度下,想炫耀一下府中獄空的祥瑞,不知會怎麼被京城士民嘲笑。
信使離開,韓岡折了一下信箋,放到了桌上。
章惇對他笑道,“之看來是真心改過了。”
韓岡則搖搖頭,“到底是真心,還是敷衍,甚至推卸,還要再等等看。”
如果呂嘉問是一開始就大張聲勢,到抓人,弄得京師人心惶惶,這就是證明他想要自己撇清自己,把責任往都堂、往宰相上推。畢竟他敢這麼做,正常的人都會認爲是奉了宰相的鈞令。
那樣的話,章惇和韓岡就得毫不猶豫地將呂嘉問給辦了。
但如果是一個人一個人地抓,慢慢來,儘量減小風波,那韓岡和章惇還能容許他一個面的結果。等一切結束之後,就安安穩穩地退下去。至於指保留權位?天底下可沒那麼好的事!
看見韓岡毫不容的態度,章惇嘆了一口氣,“希之不要一誤再誤。”
“希他不會。”韓岡說道。
這一回讓呂嘉問做的就是大清洗的差事,不論有罪無罪,是否牽涉其中,只要看起來有點關聯,就抓起來。即將離開的韓岡需要一個乾淨的京城,即將掌握大權的章惇需要一個乾淨的京城,即將展開的對遼攻略,同樣需要一個乾淨的京城。
怎麼打掃乾淨,就看呂嘉問賣不賣力了。
稍稍議論了一下,韓岡和章惇各自埋頭公事,即將大舉攻遼,一時間事務比尋常多了數倍,因而兩位宰相近幾日才需要同時留在都堂。
只是一刻鐘之後,另一個消息從開封府衙傳來,讓兩位宰相放下手中公務,面面相覷。
“白澤琰自首了?”章惇驚訝不已。
還是丁兆蘭帶著他們去的。
就連韓岡都不知該如何評價了,“還真是本事。”
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既然做出了大清洗的決定,案件的結果也就無關要了,如白澤琰這位槍手,或殺或放,本就不放在宰相們的心上了。
一切的重心還是在北方。
猜你喜歡
-
完結397 章

快穿之寵愛
作為一個合格的女配,就該惡毒邪惡千方百計各種作死勇敢犧牲給真愛們送上神助攻? 白曦笑了。 虐渣甜寵快穿,人人愛上我係列 甜甜寵寵
40.2萬字7.58 5944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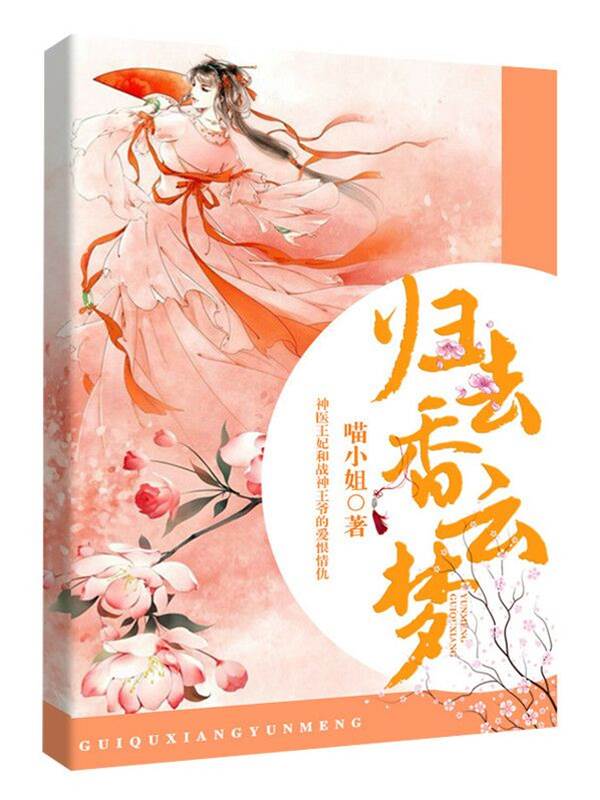
歸去香雲夢
前世女學霸意外穿越竟變成了一個傻子!賭場賺錢發家致富,英勇智鬥心機綠茶,裝傻挑逗帥氣鮮肉,卻意外落入感情陷阱......
22.4萬字5 16328 -
完結3908 章

逆天狂妃
血薇,人人聞之色變的傭兵之王。淩雪薇,被未婚夫退婚,被妹妹算計,淩府人人厭棄的廢物一朝穿越,血薇帶著研究基地和超級電腦成了淩府的廢物,從此開啟逆襲之路。天玄大陸任她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隨便拿出一把刀就是絕世神器;珍貴無比的冰晶仙露研可以大批量生產;丹藥想練就練,神器想造就造。開掛的人生是如此的寂寞
720.8萬字8 78476 -
完結321 章

病嬌暴君他有讀心術
穿成權傾朝野最終慘死的九千歲,蘇長招果斷選擇抱大腿。殊不知,暴君他有讀心術。當暴君懷疑蘇長招有異心,卻聽她心道:【狗皇帝,世上再不會有人比我更忠心。】當暴君中毒,第二天他命人全城搜尋昨夜跟他在一起的女人:【千萬不能讓狗皇帝發現我是女的。】暴君:??她是女的?這夜,暴君假借醉酒,將人撲倒:“朕想……立后!還有朕……真的很像狗麼?”蘇長招傻眼,還沒反應過來,暴君醉眼迷蒙,不大不小發出一聲:“…汪。”
67.1萬字8.18 29467 -
完結392 章

帶著嫁妝穿六零
穆清上輩子一直被家族當成準皇后培養,肩負著家族興旺的使命,卻在出嫁當天意外喪命,穿成了六零年代偏遠山村的一個奶娃娃。看著搖搖欲墜的茅草房,自幼錦衣玉食長大的穆清欲哭無淚。但這輩子的爹娘恩愛,爹爹雖然有些愛玩鬧,卻也踏實肯干,娘雖然性子軟,但…
58.8萬字8 2601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