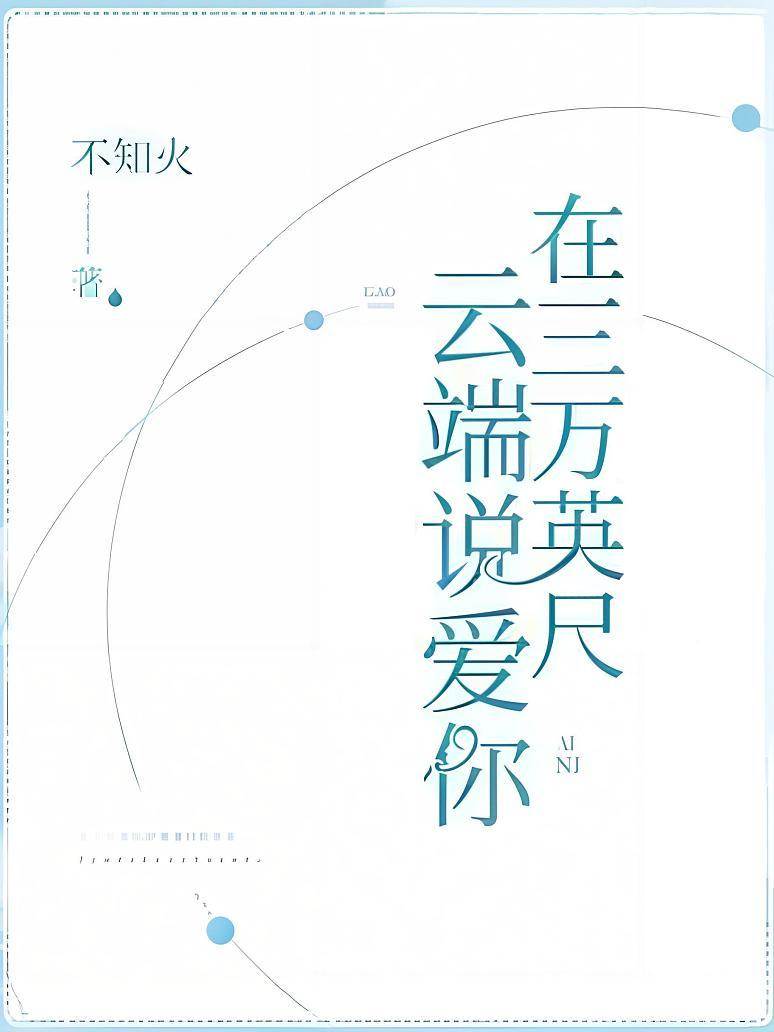《百無禁忌,她是第一百零一》 第190章:顧平生,你配不上她
顧平生將他的反應都看在眼中,眼眸嗤笑。
病房的吳雯靜的聲音還在繼續:「……孩子,沒有了。」
王文軒有些難以接:「怎麼會……怎麼會這樣?孩子是怎麼沒有的?好端端的為什麼孩子會沒有?」
吳雯靜的神之間多有些悲傷:「老頭子已經懷疑這個孩子的份了,沒有了……也好。」
「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這是我們的孩子。」王文軒沒有辦法接。
吳雯靜現在沒有時間跟他多說:「你先回去,待會兒就有人來了,你不能在這裡久待。」
王文軒還指著這個孩子能夠繼承一部分張家的家產,現在孩子沒有了,他的夢也就空了。
「走?你不告訴他,這個孩子是怎麼沒有的?」顧平生從洗手間出來,隨手將門給關上。
吳雯靜看到他的時候,顯得有些張:「是你!你沒走?!」
「你眼前的這個人,因為害怕你們之間的事暴,親手殺死了你們的孩子。」顧平生看向王文軒,在他震驚的眼眸中,說道。
王文軒轉過頭,眼睛的盯看著吳雯靜:「他說的……都是真的?」
吳雯靜了床單:「孩子是因為他才沒有的,是他要害我!」
顧平生長撐起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如果這孩子是你跟張展榮的野種,我還有可能看他不順眼,可這孩子是你跟王文軒的,我有什麼必要弄掉他?留著對我的益不是更大?」
無論此時的吳雯靜如何的狡辯,王文軒心中已經信了顧平生的話。
的確,顧平生既然知道這個孩子是怎麼回事,那留著他,讓他平安落地,就是拿在手中現的把柄,何必鋌而走險的手傷人?
在王文軒的質疑的目中,吳雯靜握了手掌,帶著怨毒的看向顧平生:「我當年就應該斬草除。」
Advertisement
是當年婦人之仁,才會留下這麼大的禍患。
顧平生薄涼的角帶著冰寒的笑意,「啪啪啪」拍了兩下手掌,洗手間的保鏢便將張之彥從裡麵推了出來。
看到張之彥帶著赤紅的目,吳雯靜頓時臉大變,「之彥……」
張之彥上的抹布已經被扯下來,他死死的盯看著病床上的吳雯靜和王文軒:「你們……真的在一起了?!」
「之彥你聽我說,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樣,我跟你王叔叔,我們隻是……」
「王叔叔?」張之彥赤紅著眼眸嘲諷的指著王文軒:「他不過就是一個下等的司機!也配做我的叔叔?!他算是什麼東西!」
麵對他的嘲諷挖苦,王文軒的臉也不太好,但是也並沒有多說什麼。
「你肚子裡的那個,真的是你們的野種?」張之彥看著剛剛流產的吳雯靜,「你一開始還打算把那個野種生下來?你們是有什麼預謀?想要跟我爭奪家產?!」
「你這說的是什麼話?你是我兒子,難道我還能害你?」吳雯靜聽到自己的兒子質疑的目的,有些傷心。
「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是不是?!」吳雯靜轉過頭惡狠狠的盯看著顧平生。
顧平生將桌上放著的手錶拿起來:「你們的戲碼我沒有什麼興趣,不過……你們的對話,已經足夠證明我的清白,至於你們的家事……我想張董,應該有時間跟你們好好的談談。」
他狹長的眼眸瞥向病房門口的方位,那裡站著一臉鐵,氣的渾都在發抖的男人——張展榮。
這一下,屋子裡的三個人的臉都變了。
吳雯靜和王文軒是事敗後的張皇無措,張之彥則是純粹的覺得難堪。
「啪。」
張展榮拽著吳雯靜的頭髮,重重的一掌扇了過去,力氣大到吳雯靜的角撕裂。
Advertisement
「賤人!你竟然真的敢給我戴綠帽子!沒有我,你現在還隻是一個村婦,我給你吃給你穿,你竟然跟一個下賤的司機茍合!」
這對於張展榮來說,絕對是奇恥大辱。
吳雯靜捂著自己的臉,麵一片慘白,知道他是都聽到了,一切就都完了。
王文軒眼看事不對,就想要走,但是卻被前來的警員撞了一個正著,警員對著照片打量了一眼王文軒,把人給攔了下來。
王文軒做賊心虛的心裡「咯噔」一下子,「你們,這是幹什麼?」
「你是王文軒?」警員問道。
王文軒遲疑著點了點頭。
警員互視一眼:「有一起案件需要你幫忙接調查,待會兒請跟我們走一趟。」
說完後,又朝著病房裡麵看了看:「誰是吳雯靜?」
雖然是在詢問,但是眼睛已經盯上了病床上的人。
張展榮的怒火還沒有出完,第二次抬起的手掌因為忽然出現的警員而頓住:「你們是來幹什麼的?」
「我們接到一起案件,對方聲稱自己被人綁架施暴,請你們配合我們的工作。」警員沉聲說道。
顧平生靜靜的聽著,削薄的瓣細微的扯起。
「是你!是你要害我!」吳雯靜看到顧平生扯起的角,像是頓時就明白了事的來龍去脈,指著他質問道。
顧平生沒有理會他的囂,而是徑直走向了前來的警員,說道:「我顧平生實名舉報,十四年前,歷臺區錦隆大廈附近,吳雯靜將一名懷胎九月的孕婦從樓梯上推下來,造一兩命!」
警員已經審問過趙芙荷,對於代的十四年前的事已經不陌生:「你是害者的?」
顧平生微微掀起眼眸:「我是……兒子。」
警員頓了一下:「……也請你跟我們走一趟吧。」
Advertisement
上巡邏車之前,顧平生眸掃過一臉慘白的吳雯靜,看來已經猜到巡捕局裡等待的是什麼,語調冰寒的吐出一個殘忍的真相:「看來,連老天都要讓你為當年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而且還是自己作死,原本吳雯靜懷著孕,顧平生一時半會兒還真的沒有辦法拿怎麼樣,畢竟華國的法律維護孕婦:在案件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審判階段,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是孕婦的,會改變強製措施,改為取保候審,如果執行刑法,會監外執行。在孕婦生產、哺期以後,才會採取收監執行。
肚子裡的孩子無異於在這個時候就是一張「護符」。
但如今也是自己親手給悔去。
吳雯靜雙眼無神的盯看著巡邏車,然後忽然之間就想要推開押解的警員逃走,顧平生嘲弄的看著的垂死掙紮。安然的坐在了自己的車上。
巡捕局。
趙芙荷已經換了一套嶄新乾淨的服,但是眼神裡始終盛著惶恐和不安,在看到吳雯靜和王文軒的那一瞬間,的開始劇烈的抖。
一方麵是因為恐懼,另一方麵是因為痛恨。
「啊啊啊啊啊」的指著兩個人,眼睛裡頃刻間就布上了紅。
為吳雯靜在看到坐在那裡的趙芙荷的時候,無聲的閉了閉眼睛,「我要找律師。」
在的話落,趙芙荷忽然之間就像是被刺激到了一樣的猛然撲上來,殘缺不平的指甲扣在的臉上,像是要把吳雯靜的臉皮整個的扣下來。
吳雯靜疼的尖,警員連忙把兩個人給分開。
但趙芙荷依舊拳打腳踢的,想要把眼前的這個人碎萬段。
顧平生就那麼坐在椅子上,看著這副狗咬狗的畫麵。
審訊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因為吳雯靜拒不配合,找來的律師也是詭辯的高手,想要洗掉吳雯靜上所有的指控。
Advertisement
顧平生出來的時候,外麵黑濛濛的一片,四方城夜裡的風像是能穿過服鑽進人的裡,一道燈猛然的亮起,轎車上下來一個包裹嚴的人,在夜中沖他揮手,喊他:「平生。」
清單的嗓音宛如是緩緩流過空穀山澗的溪流,在這無邊的夜中帶來一抹亮。
腳步尚未有所反應,角卻已經勾起,長邁開大步流星的走過去,把人抱了一個滿懷,「你怎麼來了?」
溫知夏微微揚起頭,「來接你。」
顧平生抬手點了一下翹的鼻子,「外麵冷,先上車。」
回去的時候,小佑之早就已經被哄睡了,溫知夏給他倒了杯熱水,簡單的詢問了一下巡捕局裡的事。
顧平生都一一做了回答,之後就是一場無話。
溫知夏見他像是有些疲憊,「……既然事差不多已經是板上釘釘了,先休息吧。」
顧平生點頭。
因為晚上的暖氣太充足,溫知夏口乾的醒過來,卻發現邊沒有了他的蹤影。
下樓約的看到樓下窗邊有一閃一滅的星派子,窗外月靜靜灑落,涼風習習,他的剪影落在地麵的瓷磚上。
「平生?」
依靠在窗邊的顧平生微怔,下意識的走過去滅了煙頭,抬手製止靠近的作:「你先別過來,我……剛吸了煙。」
不喜歡他煙,也不喜歡他上帶著煙草的味道。
因為溫知夏當年聽說每個煙盒上輕描淡寫的書寫著的那句「吸煙有害健康」,是一位老人奔走了數年才達的目標,老人的伴因為煙草去世,這件事像是就為了的執念,費勁了心想要提醒所有人,遠離這會逐漸累威脅命的東西,不讓悲劇再次發生。但現實很可笑的點在於,一個人用命,一個人用數載換來的一句話,非但沒有導致當年的煙草行業到影響,反而購買量不減反增。
溫知夏輕皺了一下眉頭,「怎麼起煙來了?」
他像是一個犯錯的孩子:「……沒經常,隻是偶爾。」
他其實是沒有說實話,在離開的那三年裡,陪伴他度過這慢慢長夜的,除了煙就是酒,最後還是葉蘭舟看不過去了,搬出了溫知夏,說不會喜歡上這個德行的男人。
他這才收了手。
溫知夏沒有說什麼,頓了頓以後,對上他的眼眸,這才問道:「……還在想巡捕局的事?」
顧平生微不可知的點頭,坐在一旁的沙發上,撐躬,用手撥攏了一下頭髮。
他說:「這一天,我等了十四年。」
他說:「我一直在想,如果當年我不會那麼混賬,不是選擇在家裡玩電,而是陪同一起出門,是不是……就不會死?」
他說:「如果我跟一起出門,可能後麵的事就都不會發生。的死,我也有責任……」
這些年他執念於讓吳雯靜到該有的懲罰,又何嘗不是為他自己畫地為牢。
溫知夏抱住他,「平生,這件事不要攬在自己上,吳雯靜既然想要上位,就一定會使盡千種手段,即使那天你陪著去了,也不可能阻止每一次的下手。有些人的心肝就是黑的,他們為了目的就是可以不擇手段。想要拯救一個人困難萬分,可想要傷害一個人方法有很多種,一計不還有另一計。」
顧平生著上的溫暖,手把抱坐在自己的上,讓麵對麵的坐在自己的上,麵頰靠在的脖頸上:「我隻是,隻是……心中有所悔恨。」
有些事是有辦法挽回彌補的,可當一個人不在了,就了死局,任你有滔天的本事,也無法補償萬分。
溫知夏圈住他的脖頸,兩個人的很,說:「這不是你的錯。」
「幸好,你還在,夏夏。」
真的幸好,你活著。
幸好,你還願意回到我這種人邊。
一顆晶瑩淚珠從眼角緩緩落,落在溫知夏的脖頸上,冰冷的讓心中一,「平生……」
顧平生:「嗯。」
「你還有我,還有糰子。」輕聲說道。
他細微的點頭,把人抱起來:「時間不早了,去休息吧。」
這一會兒的功夫,已經打了兩個秀氣的嗬欠。
吳雯靜犯罪故意殺人的事幾乎就是石錘,人證證都在,幾乎是辯無可辯。
眼下唯一能減輕刑罰的唯一機會,便是顧平生這個害者家屬的諒解。
張之彥來到顧夏集團的時候,整個人上都滿布著一種頹然的暮氣,眼睛裡布著,黑眼圈很明顯。
顧平生那天放在病房裡的手錶帶有錄音功能,如今張之彥控告他故意傷害吳雯靜致使滾下樓梯流產的事已經告一段落。
但所謂風水流轉,如今就是張之彥求到顧平生頭上的時候。
「你開個條件,你想要什麼?」張之彥沉聲問道。
背對著那辦公室門口的顧平生微微的轉過頭來,削薄的開闔:「我要……把牢底坐穿。」
張之彥的瞳孔收,手掌接著握起來:「顧平生,得饒人且饒人。」
得饒人且饒人?
顧平生嗤笑,眼森然:「當年害死我的母親的時候,怎麼沒有想要收手?」
狹長的眼眸瞇起來:「你手上沒有半分可以讓我饒過的東西,回去吧。」
「你難道就不想要知道……當年關於溫知夏跟我表白的錄音是怎麼回事?」張之彥沉聲問道。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顧平生唯一的肋是什麼,那大概便隻有一個溫知夏。
所有跟相關的東西,顧平生便沒有不在意的。
而這麼多年來,顧平生對溫知夏怒的事幾乎是沒有,但那份錄音始終是他心中的一道坎。
雖然後來種種皆是證明,溫知夏對張之彥不可能有什麼其他的。
但那份錄音卻是實打實的。
顧平生不可能聽錯。
顧平生抬起眼眸,眸深沉如夜。
張之彥見狀便知道,這是自己的機會:「我的要求很簡單,你讓律師出示一份和解書,表示願意原諒我母親犯下的過錯。」
顧平生磨著手指上的戒環:「我想要知道答案,大可以自己去問。你憑什麼認為,我會因為這點小事而放過吳雯靜?」
「不,你不敢。」張之彥一瞬不瞬的看著他的眼睛:「你費勁了心思的才把從徐其琛的手中搶回來,如果你開口詢問,就不怕你們之間再生?顧平生,你心知肚明,除了你,溫知夏還有其他的選擇,你……敢賭嗎?」
顧平生指尖微頓,目如勾。
哪怕是一擲千金,顧平生都不會眨一下眼睛,但……凡是涉及溫知夏,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可能,他都會畏手畏腳。
答案很顯然,他——不敢。
辦公室的時間沉寂的緩緩流逝,一秒又一分。
「說。」他薄起闔。
張之彥驀然便是鬆了一口氣。
那份錄音,那段簡短的視訊,自然不會是偽造的,不然依照顧平生對溫知夏的瞭解,頃刻間就能識破。
可凡是人便有弱點,尤其是那時創業初期,事業剛剛起步便反覆遇阻的溫知夏。
寬容這種事,通常況下都是對小孩子的,社會對於年人從來不會心慈手。
張之彥最初接近溫知夏,隻是想要看看這個能讓顧平生神魂顛倒的人到底是有什麼魔力,他也想要看看當顧平生最珍視的人上他的時候,顧平生會是什麼反應。
猜你喜歡
-
完結43 章

春色難馴
江城時家弄丟的小女兒終于回來了。 整個時家,她要星星還強塞月亮。 —————— 二中開學,時年攬著好不容易找回來的妹妹招搖過市。 眾人看著那個被時年夾在咯吱窩里,眉眼如春的小姑娘,紛紛誤會,“小嫂子絕了,絕了啊。” “想什麼呢?!”時年忿忿,“這是我妹!” 時·暴躁大佬·年,轉頭笑成智障,“歲歲,叫哥。” 此時,一位時年的死對頭,江·清貧(?)學神·頂級神顏·骨頭拳頭一起硬·馴,恰巧路過—— 椿歲哥字喊了一半,就對著江馴甜甜一聲,“哥哥!” 江馴看著這對兄妹,鳳眼微掀,漠然一瞥,走了。 時·萬年老二·考試總被壓一頭·年:“???”啊啊啊啊你他媽什麼態度?!所以為什麼你連哥都比我多一個字?! —————— 時年曾經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江馴踩在腳下,讓那個硬骨頭心甘情愿叫他一聲“哥”。 直到看見死對頭把他親妹子摁在墻角邊(沒親,絕對沒親)。 時年真的怒了,“你他媽壓.我就算了,還想壓.我妹??!!” 江馴護著身前的椿歲,偏頭懶聲,“哥。” 椿歲:“…………” 時年:“???”啊啊啊啊別他媽叫我哥我沒你這種妹夫!! —————— 小劇場: 椿歲:“為什麼裝不認識?” 江馴:“怕你喜歡我啊。” 椿歲嘁笑,“那為什麼又不裝了啊?” 春夜的風,吹來輕碎花香。 江馴仰頭,看著枝椏上晃腿輕笑的少女,低聲笑喃:“因為……我喜歡你啊。” #你是春色無邊,是難馴的執念# 冷漠美強慘X白甜小太陽 一句話簡介:我成了真千金你就不認識我了? 1V1,HE,雙初戀。不太正經的治愈小甜文。
16.3萬字8.18 6106 -
完結1181 章
余生悲歡皆為你
婚前,她當他是盲人;婚后,方知他是“狼人”。 * “你娶我吧,婚后我會對你忠誠,你要保我不死。”走投無路,喬玖笙找上了傳聞中患有眼疾、不近美|色的方俞生。 他空洞雙眸毫無波瀾,卻道:“好。” 一夜之間,喬玖笙榮升方家大少奶奶,風光無限。 * 婚前他對她說:“不要因為我是盲人看不見,你就敢明目張膽的偷看我。” 婚禮當晚,他對她說:“你大可不必穿得像只熊,我這人不近美|色。” 婚后半年,只因她多看了一眼某男性,此后,她電腦手機床頭柜辦公桌錢包夾里,全都是方先生的自拍照。 且看男主如何在打臉大道上,越奔越遠。
216.9萬字8 12334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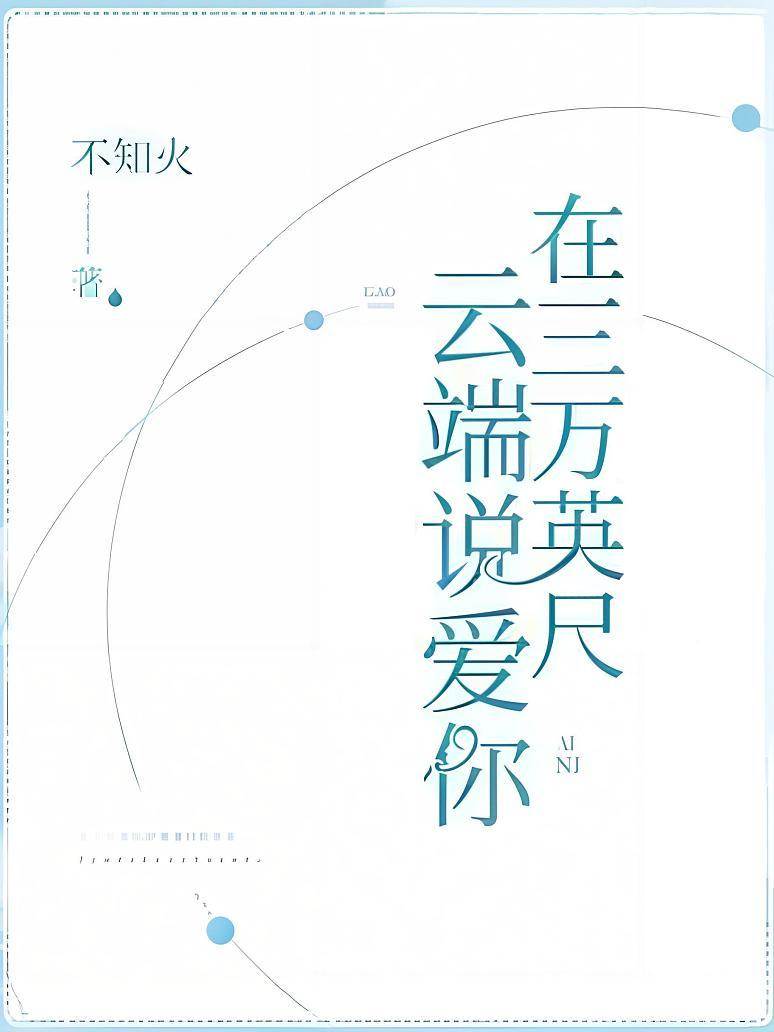
在三萬英尺云端說愛你
高考過后,楊斯堯表白周月年,兩人在一起,但后來因為性格不合,和楊母從中阻撓,周月年和楊斯堯憤而分手。分手之后,兩人還惦記著對方,幾番尋覓,終于重新在一起。周月年飛機故障,卻因為楊斯堯研制的新型起落架得以保全生命,兩人一同站在表彰臺上,共同迎接新的生活,新的考驗。
18.2萬字8 3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