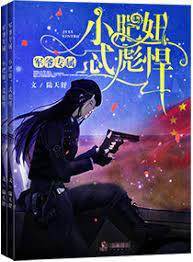《侯門棄女:妖孽丞相賴上門》 第27章 救出鬼王
這實在怪不得大圣師心大意,而是這道石門原本是由機關啟,往里推一尺后,緩緩朝旁側移開的,大圣師哪里料到它有直接被人拍開的一天?
大圣師整個人都被拍進了墻里,摳都摳不出來。
舒聽到那聲吧唧聲,覺得自己好像是撞到什麼人了,忙繞過去,開石門,看見了墻壁里的大圣師。
趕忙將大圣師拽了出來,看著奄奄一息、直翻白眼的大圣師,舒意識到自己又做了一件大錯事,急得小都開始出水波紋了:“對不起啊伯伯,我不知道你就在后面!我知道的話我一定不開門了!”
一邊說,一邊搖著大圣師,大圣師只覺自己的骨架都要被這小胖子給搖散了。
大圣師原本想要開口,可這小胖子搖得越發厲害了,這下,不僅骨架散了,連五臟六腑都仿佛移位了,他難得說不出一個字來。
舒見自己都已經這麼用力了,還是沒把這個伯伯給搖醒(已經醒了,只是在翻白眼而已啦……),不由地更加愧疚了。
都是自己不好,冒冒失失的,把這個伯伯都給拍暈了。
伯伯年紀這麼大了,不及時搶救會有生命危險的。
舒拍拍自己的小脯道:“伯伯你放心,我外公是神醫,我娘親是神醫,我也是一個小神醫,我一定會救你的!”
龍生龍,生,老鼠生的孩子會打,神醫生的孩子當然也會救死扶傷啦!
何況都救過那麼多人了,是一個有經驗的小神醫了!
舒看了看他上沒有流的跡象,嚴肅著小臉道:“你沒有外傷,應該是傷!我姥姥也是了傷,我外公給施針,幾針下去就好了!”
明明被拍斷了一條的大圣師:“……”
Advertisement
“可是我沒有針啊!”舒攤手,無奈地嘆了口氣。
大圣師心頭涌上一莫名的不祥之,下意識地把掉在后的盒子往寬袖里掩了掩。
他不掩倒還罷了,一掩,被舒給發現了。
舒一把將盒子拿了過來,打開盒子一看,竟然是一整排銀閃閃的……長釘,釘子比針要多了,不過也是尖尖的,也是長長的,還都是銀的,四舍五一下,可不就是娘親和外公的銀針了嗎?
原來這個伯伯也是一個大夫呀!
在舒的印象中,只有大夫才會隨攜帶銀針噠!
很快,舒又看見了銀針下的圖紙。
這一定就是伯伯的醫書了。
舒仔仔細細地研究了一番“醫書”,上面寫的字,看不懂啦,可是這個圖畫得很明白,知道怎麼給伯伯施針啦!
看著這不知打哪兒冒出來的小胖子,拿著一枚鎮魂釘朝他看了過來,大圣師整個人都不好了,他扭著子,想這小胖子停下,可剛一扭,舒扎歪了。
舒看看圖冊,又看看自己扎的地方,果斷把鎮魂釘拔了出來。
之所以鎮魂釘,就是因為它釘進去,傷害的不止是人的,就連神識與本元也會到極大的創傷,那種疊加而來的疼痛,絕不是捅一刀子能比的。
而對被釘的人而言,最痛苦的還不是扎進去,而是拔出來,那種連同皮與靈魂全都被撕扯的疼痛,就像是將人整個兒都給絞碎了。
原本蓄足了力氣想要嚎上一嗓子的大圣師,疼得徹底說不出話了。
被拔掉釘子的地方噴如注。
大圣師驚恐地看向舒,用所剩無幾的力氣,咬出了一口氣息:“…………”
舒擺擺小手道:“伯伯你放心,我是小神醫,我不怕。”
Advertisement
大圣師:“……”
誰擔心你怕了,不該擔心我流嗎?!
大圣師簡直要崩潰了!
舒對著圖冊,將十八顆鎮魂釘一顆一顆地給大圣師扎了進去,還不是痛痛快快地扎的,而是學著娘親與外公的樣子,一點一點轉進去的。
這特麼就更疼了……
大圣師活了大半輩子,從沒被人如此凌過,給疼得鼻歪斜,簡直都不想活了。
求給個痛快吧……
給大圣師施完針,舒小神醫“累”極了,抬手了額頭并不存在的汗水,氣吁吁地說道:“呼呼,好累好累呀!”
大圣師激得想哭,可算是結束了……
舒用圖冊扇了扇風,一扇,發現反面還有一張圖!
大圣師驚恐地瞪直了眼,不要看!不要——
舒當然是看了,看完發現新的“針灸圖”了,先前那張圖是扎前面,這一張圖是扎背面。
舒看看奄奄一息的大圣師,恍惚間明白了什麼:“難怪伯伯還沒好呢,是要扎兩次啊!”
大圣師瑟瑟發抖:不是啊不是啊!不能扎啊!救命——救命——救——命——啊——
當國師大人提著一個食盒進室時,看到的就是躺在地上早已沒了知覺的大圣師,以及一手拿著一張紙,一手拿著一釘子,在大圣師上扎來扎去的小胖子。
小胖子喃喃地說道:“是這里啊……沒扎錯啊……”
國師大人的太當即突突一跳,手里的食盒都險些給拋了出去!
他不會承認自打被小胖子了兩次,他便得了一種做害怕小胖子的病。
原本這病已經快要痊愈了,可今日過后,怕是更為嚴重了……
這小胖子,竟然用鎮魂釘把大圣師給釘了!
Advertisement
國師大人整個人都不好了。
“看見大圣師了沒有?”通道的另一頭,忽然傳來一名弟子的聲音。
另一名弟子道:“我也在找他呢,那個毒不見了,圣師殿現在都作一團了!”
二人一邊說著話,一邊朝石室走來了。
國師大人看了一眼地上的小胖子,眉心蹙了蹙,眼底浮上一抹糾結,片刻后,他把心一橫,抱起地上的小胖子,將帶去了另一間石室。
舒扭頭看到他,驚喜一笑:“誒?老伯伯,是你呀?”
國師大人沖他比了個噤聲的手勢:“噓——”
舒不懂國師大人在干什麼,可是個聽話的好孩子!
捂住小兒,眼睛亮亮地點了點頭。
國師大人又走出去,將大圣師的……,他想說尸來著,畢竟被鎮魂釘釘這樣,不死也廢了,他將大圣師拖了進來,將食盒的飯菜倒在地上,掩蓋了一灘跡。
兩名弟子進屋時,看到的就是國師大人蹲在地上收拾潑掉的飯菜,二人下意識地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鬼王,沒察覺到有什麼異常,其中一名弟子道:“琴圣師,你可看見大圣師了?”
國師大人道:“沒有。”
兩名弟子轉離開了。
國師抹了把額頭的冷汗,進石室,就要帶舒離開,舒卻跑向了跑向了躺在地上的鬼王,拿掉他上的龍潯鏈,跪在地上,崛起小屁屁,眨著大眼睛看向他:“鬼王爹爹。”
鬼王睜開了沉重的眼皮,映眼簾的一雙比星空還要璀璨的眼睛,他心口一熱,整個人都委屈極了:“吼~”
舒:“吼~”
舒自荷包里出了一顆小糖豆,喂進鬼王的里。
悉的配方,悉的味道。
Advertisement
鬼王差點哭了,為什麼糖豆不甜?
舒:過了啊!
……
兩名弟子走出小別院后,實在想不出大圣師究竟會去了哪里,明明剛剛還看見鬼姬打小別院跑出來的,鬼姬一向與大圣師形影不離……
“等等,你有沒有覺得哪里不對勁?”其中一名弟子道。
同伴問道:“你是指什麼地方不對勁?”
弟子道:“方才的室里,我好像聞到一腥氣了。”
“有嗎?”同伴只聞到了飯菜的香氣。
弟子謹慎地說道:“再去看看。”
兩名弟子折回了小別院的室,令二人驚訝的是,石室的石門卡住了,怎麼都打不開。
“有人在嗎?”
“誰在里頭?”
“開一下石門!”
“開門!開門吶!”
兩名弟子在石室中喊破嚨之際,一座古樸沉寂的石樓里,卻滿屋子都是嘎嘣嘎嘣的聲音。
一大一小坐在凳子上,連晃以及仰頭往里倒豆子的作都一模一樣。
嘎嘣嘎嘣,嘎嘣嘎嘣!
嚼豆子的頻率也一樣!
坐在對面的國師大人面如死灰,默默地往耳朵里塞了兩團大棉花。
好抓狂……好煩躁!
……
卻說另一邊,喬薇將那個純之的人自圣師殿出來后,不久就讓人發現了,當然了,只是發現純之不見了,并不知是被喬薇給走了,還以為是像二師姐那樣,自己逃跑了。
圣師殿慌作一團。
喬薇將人給了十七,讓他帶去三殿下的屋子藏著。
方才在圣師殿轉悠了一圈,已經能夠確定鬼王并不在圣師殿,現在,需要去別的地方運氣。
十七的輕功出神化,帶個人避開圣教弟子以及死士潛三殿下的屋子,毫無力。
他輕松潛進了屋子,將人塞進了三殿下的柜子,隨后,他雙手抱懷,夾著一柄長劍,死死地盯著柜門。
沒多久,柜門了,人自柜子里爬了出去。
十七一腳將踹了回去!
人被踹暈了,可不一會兒又醒了。
又爬了出來。
十七又將踹了回去。
時間,就在你爬我踹中悄然地流逝了……
……
三殿下今日也是有任務在的,這種被委以重任的覺新奇又好,難怪二表哥總要跟著表嫂出去了,從今往后,他決定也跟著表嫂混了!
三殿下帶著燕飛絕與海十三來到圣教的藏書閣。
燕飛絕與海十三是圣師殿弟子的打扮,大圣師在圣教地位卓然,三殿下的飲食起居也皆由他照看,三殿下后會跟著兩個圣師殿的弟子不算什麼稀奇古怪的事。
藏書閣的守衛客客氣氣地給三人放了行。
圣教的藏書閣極大,比族長老院的藏書閣還要大上一圈。
三殿下說道:“一層不用看了,我都翻過,全是些史書典籍,武功心法在樓上。”
三人上了樓。
海十三接到任務來到夜羅后,便潛心修習夜羅文,如今已有小,基本上都能看懂。
燕飛絕不懂夜羅文,便與三殿下一道,讓三殿下說給他聽,里頭都寫著什麼。
三人兵分兩路,將所有武功心法都翻了一遍,并沒有找到任何能夠煉化毒丹的法子。
“是不是你們記錯了?”三殿下問,“真有這種功心法嗎?”
海十三道:“你姥姥說有,應該就是真的有。”
三殿下哎呀了一聲:“你說的我都想見我姥姥了!我姥姥長什麼樣?是不是和我娘很像?”
海十三一笑:“你娘……應該更像你姥爺。”
“哦。”三殿下失,他一點也不喜歡那個把他姥姥害出家門的姥爺!
燕飛絕蹙眉道:“三殿下,圣教只有這一個藏書閣嗎?會不會還有什麼別的地方放著武功心法?”
三殿下說道:“當然有啊,那些尊主的手中就有不外傳的武功心法。”
海十三搖頭:“云夫人的意思,煉化毒丹的法子應該是在圣教的藏書閣中,不在尊主們的手里。”
“藏書閣的話……啊!”三殿下電火石間想到了什麼,眸子一瞪道,“那就只剩那里了!”
“哪里?”海十三與燕飛絕異口同聲地問。
三殿下道:“銀湖島。”
圣教占地面積極廣,有山有水,也有湖,其中最大的湖便是銀湖,三殿下來了圣教這麼久,幾乎哪兒都去過,唯獨沒去過銀湖。
銀湖上有小島,銀湖對岸似乎也有東西,不過是什麼,就不是三殿下能夠知道的了。
銀湖的岸邊有一座小木屋,小木屋往東三十步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渡口,渡口停靠著一艘烏篷船。
烏篷船每日都往返銀湖島一次,主要是輸送新鮮食材,今日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船夫在小木屋吃了一碗大廚房熬制的紅棗銀耳湯,不知怎的竟鬧起了肚子。
這一鬧,開船的時辰就晚了。
景云是在開船的前一刻爬上船的,早先在馬車上吃了太多烤全羊,口干舌燥的,又沒水喝,只得把馬酒當了水喝。
喝完就醉倒了,在金雕暖烘烘的的羽翼下睡了一覺,然后被尿給憋醒,暈暈乎乎地下了馬車。
若在以往,他就記得回去的路了,可這會子醉得一塌糊涂,哪兒還曉得東南西北?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爬上船的。
他鉆到了蓋著食材的油布底下,打了個呵欠,迷迷糊糊地睡了。
圣教沒有孩子。
船夫當然不會料到自己的船上多出了一個景云來,他拖著虛弱不已的子,將烏篷船慢悠悠地劃開了。
當三殿下一行人抵達渡口時,烏篷船已經劃到湖心了。
著幾乎消失的烏篷船,三殿下跺了跺腳:“來晚了!”
燕飛絕看了看碧波潺潺的湖水,蹲下,用手指試了試水溫:“還行,不算太冷,要不游過去?”
他話音剛落,一條食人魚自水下蹦了出來,一口咬向他的手指!
燕飛絕嚇得一屁跌在了地上!
食人魚撲了個空,牙地跌回了水中。
……
烏篷船靠岸了,原本是有人等在這邊卸貨,可船夫來晚了,等他的人已經去吃飯了。
船夫只得自食其力,可惜剛搬了一筐東西,便覺腹中傳來一陣絞痛。
他發誓他這輩子都沒這麼疼過,他到底吃了啥?!
船夫手中的筐子吧嗒一聲掉在了甲板上,巨大的靜,將景云驚醒了。
景云挑開眼前的油布,一陣冰冷的湖風吹來,景云的酒醒了一半!
這是哪兒?
他怎麼會在船上?!
景云了眼,眼前的景象沒變,他看著完全陌生的環境,愣愣地站起來,走下船,上了岸。
島上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陌生的小道,陌生的花園,以及……陌生的屋子。
景云找了幾間小木屋,似乎都沒有住人。
他繼續往前走。
他終于看見人影了!
是兩個提著籃子的姑娘,二人有說有笑,著另一個方向走去。
景云邁開小短兒追了上去,可當他繞過最后一間小木屋,以為能看見二人的影時,卻又什麼也看不到了。
“景云……”
一道溫的聲音自景云的后響起,空靈又虛無而縹緲,聽得人如置夢中。
景云愣愣地轉過來,卻沒看見任何人影。
“景云……”
溫又空靈的聲音再一次地若若現地響起了。
景云長了脖子,朝前方張。
“景云……”
景云順著聲音,往右前方走了過去。
不知走了多久,他看見一座五十的水晶宮,宮殿奐,像是畫上的仙宮一樣。
猜你喜歡
-
完結2261 章

影視世界當神探
陸恪重生了,還重生到了美國。但他漸漸發現,這個美國并不是上一世的那個美國。 這里有著影視世界里的超凡能力和人物,他要如何在這個力量體系極其可怕的世界存活下去? 幸好,他還有一個金手指——神探系統。 一切,從當個小警探開始……
416.5萬字8.18 46115 -
完結358 章

嫡女無雙:惹火棄妃太搶手
手握大權卻被狗男女逼得魚死網破跳了樓。 可這一跳卻沒死,一眨眼,成了草包嫡女。 不僅如此,還被自己的丈夫嫌棄,小妾欺負,白蓮花妹妹算計。 你嫌棄我,我還看不上你;你欺負我,我便十倍還你;白蓮花?演戲我也會。 復雜的男女關系,本小姐實在沒有興趣。 和離書一封,你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 原以為脫離了渣男是海闊天空,可怎麼這位皇叔就是不放過她? 說好的棄妃無人要,怎麼她就成了搶手貨了?
81.3萬字8.09 94242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3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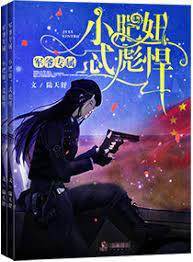
軍爺專屬:小肥妞,忒彪悍!
身為雇傭兵之王的蘇野重生了,變成一坨苦逼的大胖子!重生的第一天,被逼和某軍官大叔親熱……呃,親近!重生的第二天,被逼當眾出丑扒大叔軍褲衩,示‘愛’!重生的第三天,被逼用肥肉嘴堵軍大叔的嘴……嗶——摔!蘇野不干了!肥肉瘋長!做慣了自由自在的傭兵王,突然有一天讓她做個端端正正的軍人,蘇野想再死一死!因為一場死亡交易,蘇野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色誘……不,親近神秘部隊的軍官大叔。他是豪門世家的頂尖人物,權勢貴重,性情陰戾……一般人不敢和他靠近。那個叫蘇野的小肥妞不僅靠近了,還摸了,親了,脫了,壓了……呃...
96.9萬字8 14612 -
完結529 章
冷王追愛:萌妃輕點寵
一朝穿越,慕容輕舞成了慕容大將軍府不受寵的癡傻丑顏二小姐,更是天子御筆親點的太子妃!略施小計退掉婚約,接著就被冷酷王爺給盯上了,還說什麼要她以身相許來報恩。咱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躲躲藏藏之間,竟將一顆心賠了進去,直到生命消亡之際,方才真切感悟。靈魂不滅,她重回及笄之年,驚艷歸來。陰謀、詭計一樣都不能少,素手芊芊撥亂風云,定要讓那些歹人親嘗惡果!世人說她惡毒,說她妖嬈,說她禍國?既然禍國,那不如禍它個地覆天翻!
89.6萬字8 474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