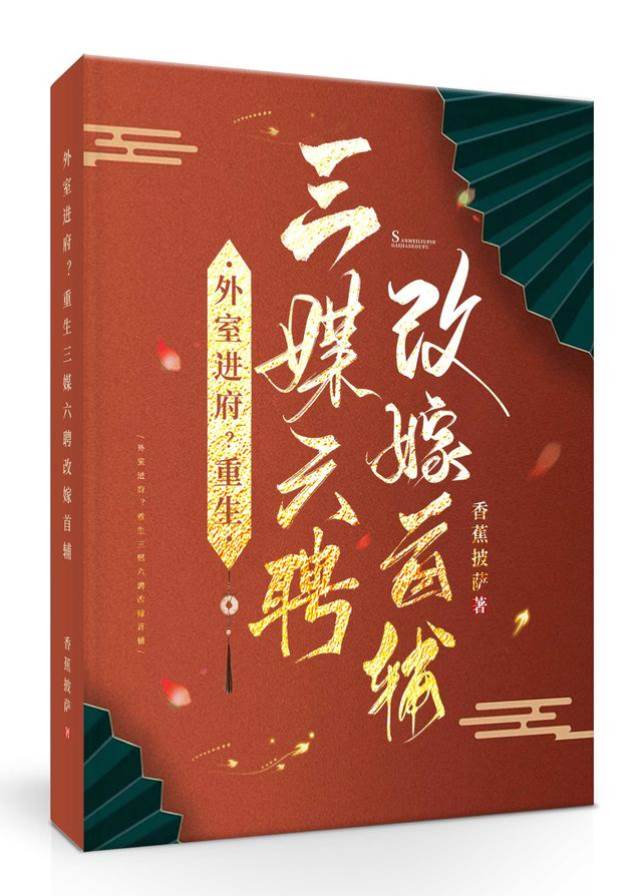《簪中錄》 第112章葉底游魚(2)
朝初升,照徹大理寺。剛爬上樹梢的日頭便展現出自己的威力,今天注定會是一個炎熱的天氣。
今日三法司會審,史臺、刑部、大理寺,三位長一字排開,坐于上首。按例,三司使會審時,大理寺示證據、定案,刑部下判決,史臺監審。
大理寺一直都是卿主持事務,坐的是崔純湛。他看見跟著李舒白進來的黃梓瑕,以一臉幽怨的神看著,就只差對著喊——求你了,今天千萬別出聲,就這麼結案吧!
刑部尚書王麟,當然記得黃梓瑕是將王皇后送太極宮的罪魁禍首,所以瞧都不瞧一眼,只對著李舒白微微頷首。
史臺來的是史中丞蔣馗,老頭兒顯然對于自己居然淪落到監審這種殺人案而不齒,只是礙于死者中有個公主而勉強坐在案前,袖著手,閉目養神。
所有與此案關涉人等一一到來。
駙馬與鄂王在堂邊坐著,駙馬呆著鄂王帶來的錦盒上的花紋,心神恍惚,面容憔悴。
垂珠落珮墜玉傾碧四個侍站在他們后,個個面容惶看,不知自己究竟會有何遭遇。
張行英與滴翠并肩站在堂下,滴翠形容消瘦,面容蒼白。張行英悄悄地握住的手,以示安。
呂至元蹲在他們不遠的涼地,埋著頭,盯著地上的青苔。
從大牢里被提出來的錢關索,萎頓地靠著梁柱坐著,整個人焦黃灰暗,一直都在抖,面如死灰。
在所有人中,唯有周子秦神如常,依然穿著一鮮艷服,眉飛舞地沖黃梓瑕和李舒白招手:“王爺不會怪罪吧?因為這個案子我跟了很久,所以雖然沒有召喚,我也來旁聽了!”
“隨意,只要待會兒沒有你時,你不能出聲。”李舒白一口就斷絕了他可能會鬧的幺蛾子,周子秦只能苦著一張臉點點頭。
Advertisement
大理寺給李舒白搬了椅子,坐在鄂王旁邊。黃梓瑕和周子秦站在他后,一個一臉沉郁,一個東張西。
李潤轉頭看向黃梓瑕,面容上是慣常的那種和笑意:“楊公公,此案既然已經揭曉真相,想必你也終于可以松口氣,休息一下了,怎麼還是心事重重、思緒萬千的模樣?”
黃梓瑕尷尬低頭道:“是,多謝鄂王爺關心。”
李潤又悄悄問李舒白:“四哥,你讓我把那張畫帶過來,是有什麼用嗎?”
“嗯。”李舒白點頭,說,“此案種種手法,應該就是從父皇的筆中而來。”
“可……父皇去世已有十年,如今怎麼忽然又牽扯到這樣一個案件?”李潤疑地問。
李舒白還未回答,外邊宦列隊進來,皇帝已經到來。
與他一起進來的,還有郭淑妃。大理寺的人趕去后面搬了椅子過來,讓坐在皇帝后面。
等一干人等坐定,崔純湛一拍驚堂木,下面一片肅靜。
錢關索被帶上來,同時呈上他這幾日在大理寺中的供詞,已經謄寫清楚,只等他簽字畫押。
“錢關索,你殺害同昌公主,魏喜敏,孫癩子三人,證據確鑿,還不快將作案經過一一供出,認罪伏法?”
錢關索被折騰這幾日,原本白胖富態的人如今瘦了一圈,雖然還胖,卻已經喪盡了氣神,只剩得一死氣。
他披頭散發穿著囚,跟個豬尿泡似的癱在地上,聽到問話,他似乎想用雙手撐起子回話的,但那雙手已經滿是燎泡,又在水里被泡得反白,十手指上連一片指甲都不剩了。他吃不住痛,只能依舊癱在地上,低聲哼哼著:“認罪……認罪……”
“從實招來!”
Advertisement
“罪民……覬覦公主府的奇珍異寶,所以買通了公主邊的宦魏喜敏,與他一起盜取了金蟾。一切都是罪民瞞著家人的……我家人絕不知曉……”
崔純湛沒理他,徑自問:“魏喜敏因何而死?”
“只因……我們分贓不均,他和我翻臉,罪民怕此事泄,就……在薦福寺和他一起參加佛會時,借著蠟燭起火而將他推到火里燒死了……”
“孫癩子的死又是為何?”
“因為……”錢關索木然地蠕著,臉呈現出一種異樣的死灰,那眼睛深陷,就像一個,什麼亮都沒有,“罪民殺死魏喜敏時,恰好被他看見了,后來他勒索我,我就趁著手下人清理下水道時,把人支開后,爬進去把他也殺了……”
崔純湛不聲地看了皇帝一眼,見他只凝神端坐,稍微放下了心,于是又問:“那麼你又為何殺害同昌公主?”
“罪民……罪民……”他蠕著,眼睛看向坐在后面的皇帝幾人,終究還是不敢開口。
崔純湛一拍驚堂木:“若不想再皮之苦,就快點從實招來!”
“是……是罪民賊心不改,聽說公主夢見自己最珍的九鸞釵不見了,所以罪民就又潛公主府竊得九鸞釵……誰知那天在街頭,罪民一時興起拿出來看時,居然被公主看見了,追到僻靜,罪民一時失手,就……就……”
皇帝的臉變得鐵青,他死死盯著錢關索,憤恨而絕,在這一刻,他恨不得自己是個普通的坊間平民,這樣,就能放任自己撲上前去,將面前這個殺害自己兒的惡人狠狠痛毆一頓,至,能讓自己的怨恨發泄一些。
郭淑妃咬牙切齒,呼的一聲站起來怒吼道:“皇上,必得當堂殺了他,為靈徽報仇!”
Advertisement
皇帝抬起手,制止住,咬牙道:“有三司使在,何須我們!”
黃梓瑕站在李舒白的后,專注聽著錢關索的供詞。
錢關索上遍鱗傷,聲音半是半是哼哼:“一切……只與罪民一人有關,罪民的妻兒親友并不知曉……罪民認罪……”
“既然如此,簽字畫押。”崔純湛將大理寺丞記錄的供詞拿過看了一遍,讓人拿去給錢關索畫押。
錢關索委頓在地,勉強撐著看了一遍,然后用那雙已不堪目的手握起筆,合起眼睛,就要簽上自己的名字。
就在此時,忽然“啪嗒……”一聲悶響,打破了堂上的肅靜。
是站在堂旁的滴翠,可能是被嚇到了,再加上本來就弱,竟一下子癱倒在地,昏了過去。
而錢關索的手一抖,那支筆上的墨頓時在供詞上畫了一道長長的痕跡。
站在滴翠邊的黃梓瑕,趕抬手將扶住。張行英焦急地看著滴翠,見兩眼渙散,全冰冷,趕對堂上說道:“崔大人,阿荻……滴翠自大理寺回來之后便虛弱,恐怕這況,無法再在堂上聽審了……”
崔純湛看著青灰的臉,也覺得況似乎很不好,便回頭看皇帝。
皇帝只盯著錢關索,問:“是誰?”
“是原先的一個嫌犯,如今事實證明,確與此案無關——因公主薨逝之時,就被關押在大理寺。”
皇帝揮揮手,說:“這種閑雜人等,快抬出去。”
張行英趕抱起滴翠,想要帶著出去,崔純湛又說道:“張行英,你也是本案相關人等,不宜擅自離堂。”
李舒白便示意景祐扶住滴翠,讓他帶著出去。
滴翠茫然無知,記得剛才自己明明好好的,結果黃梓瑕一自己的肩膀,聞到一香味,就倒了下去。而這麼一下暈過去之后,也馬上就恢復了。
看了看張行英,正想告訴他自己沒事,卻聽到黃梓瑕在的耳邊輕聲說:“逃!”
愕然睜大眼睛,想看一看黃梓瑕的神,問明對自己這樣說到底是什麼意思,但黃梓瑕卻已經越過,站到了堂前。
滴翠被景祐扶著,走到門口。大理寺的門吏指著滴翠問:“公公,這是怎麼回事?”
“好像犯病了,皇上口諭,將立即抬出去。”說著,景祐放開了,示意,“還不快走?”
滴翠站在已經十分熾熱的夏日之下,看了看大理寺的大門,覺得大腦微微暈眩。
黃梓瑕在耳邊說的話,又回響——
“逃!”
恍惚地一遲疑,然后立即轉過,快步向前走去,匯了京城朱雀大街的滾滾人之中。
猜你喜歡
-
連載1900 章

嫡女驚華
鳳驚華前世錯信渣男賤女,害的外祖滿門被殺,她生產之際被斬斷四肢,折磨致死!含恨而終,浴血重生,她是自黃泉爬出的惡鬼,要將前世所有害她之人拖入地獄!
194.9萬字8.18 337396 -
連載162 章

東宮美人
宋懷宴是東宮太子,品行如玉,郎艷獨絕,乃是世人口中宛若謫仙般的存在。南殊是東宮里最低下的宮女。她遮住身段,掩蓋容貌,卑微的猶如墻角下的殘雪,無人在意。誰也未曾想到,太子殿下的恩寵會落在她身上。冊封那日,南殊一襲素裙緩緩上前,滿屋子的人都帶著…
51.2萬字8 8875 -
完結919 章
娘子很剽悍
前世她不甘寂寞違抗父命丟下婚約與那人私奔,本以為可以過上吃飽穿暖的幸福生活那知沒兩年天下大亂,為了一口吃的她被那人賣給了土匪。重生后為了能待在山窩窩里過這一生,她捋起袖子拳打勾引她男人的情敵,坐斗見不得她好的婆婆,可這個她打架他遞棍,她斗婆婆他端茶的男人是怎回事?這是不嫌事大啊!
85.9萬字8 2980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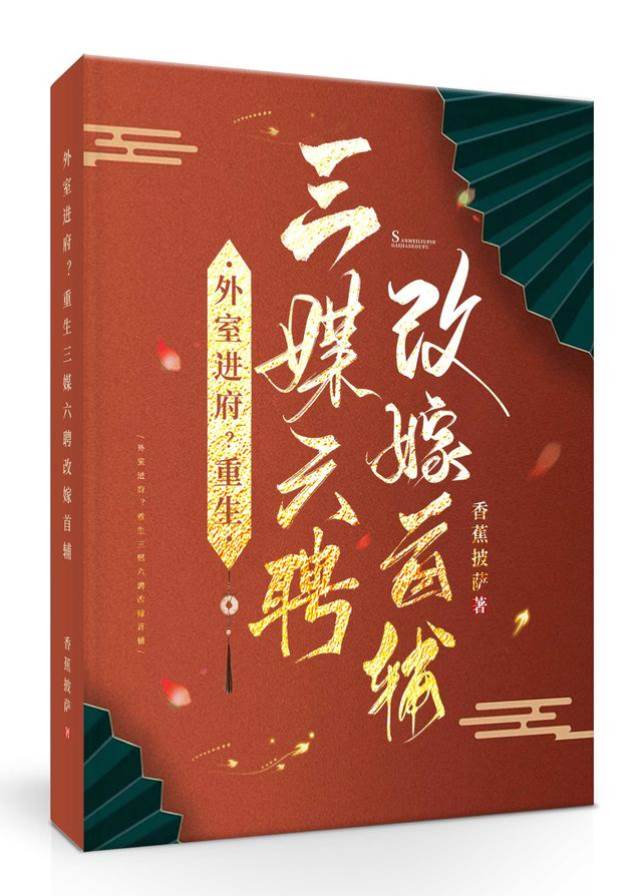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08 53539 -
完結239 章

寵妾滅妻奪嫁妝?廢你滿府嫁皇家
前世,謝錦雲管理後宅,悉心教養庶子庶女,保住侯府滿門榮華。最後卻落得一杯毒酒,和遺臭萬年的惡毒後母的名聲。死後,她那不近女色的夫君,風光迎娶新人。大婚之日,他更是一臉深情望着新人道:“嬌兒,我終於將孩子們真正的母親娶回來了,侯府只有你配當這個女主人。”謝錦雲看到這裏,一陣昏厥。再次醒來,重回前世。這一次,她徹底擺爛,不再教養狼心狗肺之人。逆子逆女們若敢惹她,她當場打斷他們的腿!狗男女還想吸血,風風光光一輩子?做夢!只是,她本打算做個惡婦,一輩子在侯府作威作福。沒想到,當朝太子莫名伸手,先讓她成爲了下堂婦,後又欽點她爲太子妃?她還沒恍過神呢,發現一直仇恨她的庶子庶女們,一個個直呼後悔,說她纔是親孃。昔日瞧不起她的夫看,更是跪在她面前,求她再給一次機會?
44.2萬字8.18 36260 -
完結185 章

小娘,你也不想王府絕後吧
西南王季燁出殯那天,失蹤三年的長子季寒舟回來了。爭名,奪利,掌權,一氣嗬成。人人都說,季寒舟是回來繼承西南王府的,隻有雲姝知道,他是回來複仇的。他是無間地獄回來的惡鬼,而雲姝就是那個背叛他,推他下地獄的人。她欠他命,欠他情,還欠他愛。靈堂裏,雲姝被逼至絕境,男人聲音帶著刻骨的仇恨與癲狂“雲姝,別來無恙。”“我回來了,回來繼承父王的一切,權勢,地位,財富……”“當然也包括你,我的小娘。”
27.5萬字8.33 87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