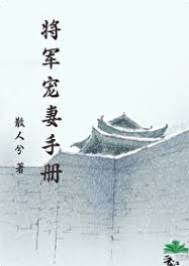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離凰》 第56章 叫我姑奶奶 為鑽石過600加更
眾人皆是一驚,萬萬沒想到半路上竟然殺出個程咬金。而這程咬金一襲綠蹁躚,還是個段纖瘦的子。這子眉目姣好,半斜著子坐在樓梯扶手上,懷中抱著一把劍,顯然是會武功的,而且……是如何進來的,什麼時候進來的,誰都沒有注意。
「你是什麼人?」為首的歹人厲喝。
「憑你,還沒資格知道我的名字!」步棠淡淡然抬頭,對上沈木兮時,竟浮起滿臉戲之,「又見麵了,病人!」
沈木兮看了看春秀,再瞧著自己,想來對方說的是。
「你在說我嗎?」春秀上前一步。
「咦……」步棠搖搖頭,「你得去掉中間那個字!」
春秀掰著手指頭,「病人,病……人?」
「別鬧了!」沈木兮心頭微沉,「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為何要殺我?平白無故的,我沈木兮自問沒有虧待過任何人,對於傷病皆一視同仁,予以診治,為何……」
「殺人哪有那麼多的原因?」步棠輕飄飄的從扶手上躍下,形一晃已經擋在了樓梯口,略帶嫌棄的沖著劉得安擺擺手,示意他靠邊站,「這些人平素就是打家劫舍的匪盜,你們運氣不好,投宿在他們的老巢,那還不得一鍋端了?」
老巢?
劉得安愕然,「這裡是……」
「這是山賊窩!」步棠翻個白眼,「虧你還是吃公糧的,竟是這點眼力見都沒有?不過呢,盜亦有道,你們這幫死東西,今兒敢姑的眉頭,真是不要命了!」
歹人愕然,略有所思的麵麵相覷,一時半會的鬧不明白這人的來頭。
「你……」為首的歹人握著刀,方纔的盛氣淩人之勢漸漸消散,「到底是誰?」
「姑的名號都不知道,還敢在江湖上混?老壽星吃砒霜,我瞧你是嫌命太長。」步棠懷中抱劍,居高臨下的睨著他,「聽過十殿閻羅嗎?」
Advertisement
「咣當」一聲響,為首的歹人竟然麵驟變,手中的大刀登時落地,「十殿閻羅?冥君嗎?」
「喲,還知道呢?」步棠輕哼,「不算太蠢嘛!今兒要是我家冥君來了,估著你們都得完蛋,剁胳膊剁那都是輕的,皮拆骨,碾骨灰,那才痛快呢!」
一時間,場麵僵持不下。
春秀不解,低低的問,「什麼十殿閻羅?」
劉得安低聲解釋,「聽說是江湖上的邪魔外道,人人都聞之變,殺人手段格外狠辣。為首的是冥君,底下有十位護法,一個個武藝了得,但是誰都沒真正見過冥君,護法倒是在江湖上經常行走。但凡招惹了這十殿閻君,那可就是滅頂之災。」
「比皇帝還厲害嗎?」春秀瞪著眼睛問。
劉得安「嘖」了一聲,「兩碼事,朝廷不管江湖事,江湖人不得手朝廷之事,往來都是有規矩的,如此才能相安無事,否則還不得把天都個窟窿?十殿閻羅饒是武功再高,能敵得過朝廷百萬大軍?不是能相提並論。以後別問了,仔細禍從口出!」
春秀趕閉,可不敢再問。
「怎麼,想試試?」步棠不溫不火的問,「冥君定下的規矩,爾等都聽過吧?若是切磋,得提前說,若是真刀真槍的來,不死也得留下一條胳膊。你們自己選!」
「老大,這妞年輕輕的,八是糊弄你!」底下人說。
為首的打了個嗝,「你特麼是想老子死?萬一真的是冥君的人……」
「老大,怎麼辦?錢都收了!」底下人戰戰兢兢的問,「咱好歹也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若是不乾事,萬一拆了咱招牌,江湖上的人還不得笑死?何況底下一大幫兄弟張等著吃,總不好把錢再吐出去吧?連兵都殺了,咱還有什麼可猶豫的?」
Advertisement
這話說得極是,兵都殺了,隻要這些人回到東都,到時候朝廷還不得派人來剿匪?
不,不能留活口。
為首的打定主意,「給我殺!」
音落瞬間,所有人一擁而上。
劉得安舉劍沖,卻被步棠一個眼神給了回去,這丫頭眼神太狠,何止是狠,簡直是殺氣騰騰。就沖這子勁兒,絕對不是泛泛之輩。
事實證明,步棠不隻是說說而已,能說出這些話,全然是有底氣的。冷劍出鞘,速度快如閃電。
饒是劉得安為侍衛統領,對付這些莽漢也需要一定的氣力,莽漢興許武功不高,但是力氣著實太大,震得他手中的劍嗡嗡作響,握都握不住。
卻見步棠若遊龍,冷劍雖然出鞘,但沒有使全力,隻是在纏繞,而這些壯漢竟沒能再往前踏過半步。顯然,不想在這裡使出真功夫,畢竟還有朝廷的人。
壯漢們氣籲籲,最後步棠自個也煩了,忽然收劍歸鞘。
眾人還沒回過神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驟然間一道寒掠過,一條快速從步棠的袖中彈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纏在為首的歹人脖頸上。
「住手!」男人驚呼,「都別過來!」
「很識相!」步棠冷笑,「再過來,我就擰斷他的脖子,當然,他死之後就到你們了!」
四下一片寂靜無聲。
步棠回頭著劉得安,「我且要個承諾,這是江湖人的事兒,能否不手?回去之後,可否讓你的部下都閉,誰敢泄誰就得死!」
劉得安綳直了子,沒有回答。
「,或者不,給個痛快話!」步棠道。
「!」春秀連忙應答,推搡了劉得安一把,「大家都死在一塊,你就高興了是嗎?要死你去死,可別連累咱們!」
Advertisement
劉得安皺眉,「,但是……我想知道是誰在幕後指使他們來殺沈大夫?」
「這事不用你提醒!」步棠指尖微彈,瞬時收。
疼得那人吱哇,「別!別!是、是一個男人,一個男人給了我們一筆錢,讓咱們在這裡留意,如果有軍行過看看是否有兩個人,一個胖一個瘦,殺了瘦的就!」
「這男人是誰?」劉得安忙問。
為首的急忙搖頭,「咱雖然是匪盜,可盜亦有道,素來不截朝廷的人,這是江湖上的規矩。何況咱們打家劫舍的,從不傷人命,隻是近段時間生意不大好,所以不得已才幹了這一票。連兄弟們都早做好了準備,鎮子上的人都提前轟走了!姑娘,咱真的……」
「姑!」步棠冷哼,「真是一幫廢!」
「姑,姑!」所有匪盜都給步棠跪下,「咱們也是混口飯吃,不容易啊!您高抬貴手,放了咱老大,咱給你磕頭了!」
沈木兮和春秀麵麵相覷,方纔那子盛氣淩人的勁兒呢?怎麼都了一幫慫蛋?
步棠覺得無趣,興緻缺缺的收回,了自個的腕部,「說實話。」
「那男人指名道姓要殺沈木兮,黑蒙麵的,咱也不知道是誰,也沒報上名號!」為首的男人捂著脖子,掌心裡有些跡,方纔劃破了他的皮,所幸步棠手下留,否則這脖子真的要被絞下來。
如此,男人心存激,「不過當時我跟他手來著,武功路數格外詭異,我在他手底下走不過兩招,在江湖上我花老七也是有名頭的,沒想到遇見個高手。所以我當時問他來著,為什麼不自己手,他讓我別問,給了錢就走了!」
「真的真的,姑,老大說的句句屬實!」底下人齊聲應合,「那男人來無影去無蹤,著實不知道他是誰,反正就是……買沈木兮的命,也沒說失敗了會咋樣。」
Advertisement
男人?
買命?
劉得安心有餘悸,回頭再看沈木兮,但見麵青白,額頭上冷汗涔涔而下,子有些搖搖墜。心道一聲不好,劉得安慌忙上前,「沈大夫?」
沈木兮眼一黑,登時往後仰去。
春秀駭然,「沈大夫!」
「花老七,姑記住你了,若是你有半句假話,我一定會殺了你!滾!」步棠轉便走,沈木兮業已暈厥,子燒得滾燙。
眼下,還是救沈木兮要,其他的容後再說。
沈木兮隻覺得昏昏沉沉,夢裡又見到了兒子,了手,卻怎麼都不到孩子的臉,無奈的著孩子漸行漸遠,「郅兒……」
沈郅長大了,即便孤一人,也不會讓自己吃虧。
就好比現在,雖然離王府,寄人籬下,可他很清楚如果自己一直人欺負,改日這些奴才們也會騎上頭來。既然薄鈺自個送上來,豈能與他客氣!
沈郅想明白了,他必須在娘來離王府之前要個立威,如此娘以後的日子才能好過。既是要立威,拿這離王府的小公子下手,自是最好不過。
「你為何在這裡?」薄鈺衝上來,他知道問夏閣代表著什麼,也明白這些年饒是母親都不被允許踏的地方,忽然被其他人踏,意味著什麼?
薄鈺可以想象,沈木兮母子會在將來的某一日,徹底取代他與娘親的位置。
他不允許!
決不允許!
沈郅直腰桿,「我不止要進來,還要住下來,就住在這裡!」
「憑什麼?」薄鈺攥拳頭。
「就憑我是你爹請來的貴客!」沈郅倨傲相對。
薄鈺氣急,對著沈郅就是一掌,哪知沈郅早就料到他會有這一招,眼疾手快抓住了薄鈺的手腕,反手就是一記響亮的耳還回去。
「啪」的一聲脆響,薄鈺狠狠摔在地上……
猜你喜歡
-
完結250 章

將門嫡女:攝政王彆囂張
她身為二十一世紀的女間諜走個路被一道雷劈穿越到了將軍府嫡女身上,本想著安安靜靜的生活,再找個金龜婿,冇想到兩個庶女姐姐一點也不安分,多次找麻煩,姨娘更是想儘辦法上位,一場刺殺遇到了眾女的夢中情人——攝政王,就因為一次英雄救美就被某個囂張自大的無賴纏上了,偷偷逃跑遇到了白衣飄飄的美男,還冇勾搭就被某人扛了回去,攝政王有種你就放我下來,我不要你了!
43.8萬字8 7526 -
完結1254 章

農家小悍妃:帶著全家討生活
顧梅朵,穿成古代九歲小女孩兒,父母兄弟老實,爺奶叔伯極品。且看她天生神力,身帶空間,如何契神獸,護家人,斗極品,抱美男,發家致富,一路瀟瀟灑灑,自由自在………
222.4萬字8.18 354174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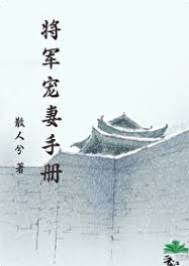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
完結100 章

山君
蘭山君孤兒出身,長在淮陵,吃百家飯長大,學得一手殺豬的本事,本是要開一個屠宰場的。誰知老天給她開了一個玩笑。 十六歲那年,她被接回了洛陽的鎮國公府,成了國公府第流落在外的嫡次女。 最初,她以爲這是老天看她殺豬太可憐給的恩待。後來又過了十年,她戰戰兢兢討好家人,汲汲營營嫁人,備受十年白眼,被送去暗不見天日的院子裏關着時,這才恍然發現,從鄉野來京,應當是她殺豬殺多了老天給的懲罰,而不是恩待。 此後又是一年,她被關在小院子裏看不見天日,不知日月更迭,冷菜餿飯度日,受盡苦楚,卻依舊是不甘不願,不敢死去。 唯一能聊慰苦悶的是,在黑暗之中,她摸到了一本書。 窗戶未曾封死,依舊透進了一縷春光。 她慢慢的挪到窗邊,藉着這屢光去看—— 這是一本手札。裏面記下了一個少年六歲到十六歲的感悟。有滿腔熱血,有遠大志向,他覺得自己像是一把利劍,只等着君王拔它出鞘。 她倒是認得執筆者。是她被送離洛陽那天,也同樣登上斷頭臺的鬱清梧。 所以重回十六歲,她與鬱清梧第一次相見時,便覺得他是一位可悲的紙上摯友。 等她在洛陽裏面艱難的重掌命運,偶然忽視一個個聲音,從春日裏的光曦窺見了他內心的躊躇不前,糾結痛苦卻又無愧於心的大志,毅然決然要走向一條死路時,她心裏突然生出些鬱怒來。 他們的命運何其相似,都不應死在權貴的愚弄之下。 她和他,都該活下來。 —— 遇見蘭山君前,鬱清梧寫札記:先生,天下,百姓。 遇見蘭山君後,鬱清梧寫札記:山君,山君,山君。 #山君倔得很,但沒關係,我會低頭# 他心隨她動,低頭哀求,“山君,我試着剋制過了。”
53萬字8 241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