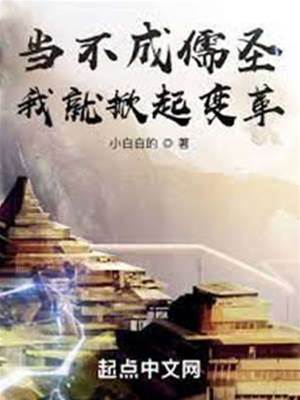《良田喜事:腹黑夫君美如花》 第141章 第141章 你打他了嗎?
夏氏將青菜老掉的梗撇去,把葉裝進菜盆裡,菜梗折斷時發出清脆的聲音。書趣樓()作嫻,過了一會兒才聲道“我們阿娬喜歡不是嗎?”
孟娬笑意明地點頭。
夏氏道“娘不阻止你們在一起,但也不會讓你們眼下就親,起碼不能讓你立刻就嫁給現在這樣的他。這婚約是有條件的,等他好能站起來以後,你才能與他完婚。”
孟娬仔細回憶了一下婚約上的容,震驚道“還有這個條件嗎?我怎麼沒看見?”
夏氏看一眼,道“婚約上沒寫,這是我和王行私下定的協議。”
孟娬眨了眨眼,“那要是他一直站不起來怎麼辦?”
夏氏道“王行會主提出解除婚約。”
孟娬蹭地站起來,道“你們怎麼能背著我簽這種不平等條約!我不乾,他是殘疾我也要!”
夏氏又看了一眼,然後恨鐵不鋼地道了一句“就你這出息!”
往後,街坊鄰裡,但凡有人問起,夏氏都會鄭重地與別人說,王行是孟娬的未婚夫。
這已經不僅僅是口頭上說說的,而是正式寫下了婚約的。
不想第二天張大娘就找上了門,也顧不上和夏氏的鄰裡和氣了,臭著一張臉,登門來討說法。
張大娘指控馮纔在巷子裡遇到了王行,結果被王行打了,折了雙手不說,到現在都還躺在床上起不來。
大夫說馮才起碼至要休養十天半個月,花了醫藥費不說,還要耽擱做工,必須要讓夏氏賠償損失。
前些天裡張氏對夏氏還有說有笑、熱洋溢,大抵也沒想到,夏氏的態度會這麼堅決,當真要讓一個殘廢當自己的未來婿,使得張氏的算盤落空,於是說翻臉就翻臉。
夏氏對張大孃的指控也是一頭霧水,把殷珩出來,道“王行,你打馮才了嗎?”
Advertisement
孟娬興沖沖地看著殷珩,心裡想著那馮才委實該打,阿珩要狠狠揍他才行!阿珩肯定是為了纔打架的,真是想想都覺得好興!
結果殷珩一臉平常地問“馮纔是哪個?”
夏氏道“就是前天來過的張氏的表侄。”
殷珩隨意地低頭牽了牽雪角,淡淡道“沒打過。”
孟娬憾地嘆了口氣。
張大娘不信,道“你還不承認,我表侄都親口說了,說就是你打的!”
殷珩抬目清淡地看著,道“我不是個廢麼,打得過兩條健全的?”
張大娘一噎,接不上話來,後氣呼呼道“可他都被打那樣了,總不會是冤枉你!”
這一鬧,家門口外麵圍了一些看熱鬧的鄰裡,任誰看到殷珩坐在椅上,都不大相信他能打得過四肢健全且油頭油的馮才吧。
於是便有人問“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呢,我看他也不像是能手的人啊。”
張大娘一口咬定道“能有什麼誤會,就是他乾的!”
殷珩挑了挑眉,道“那便讓你的表侄過來說說看。先看看他上是否有傷,再聽他說說是不是我打的。”
大家點頭,都覺得殷珩說得非常在理。
要指認一個人,當然得有證據。現在馮才沒來,誰知道他有沒有傷;也沒聽他親口指認,誰又知道是不是張氏胡說呢。
張氏自知自己勢單力薄,這樣容易理虧,便道“那好,你等著,我讓我那表侄親自來說!”
張氏走後,孟娬就看向殷珩,問“阿珩,你昨天在小巷裡遇到了馮才嗎?”
殷珩道“嗯,遇到了。”
昨天正好他單獨出門,和張氏所說的馮才被毆時間正好吻合,他縱使是想瞞也瞞不過去。
孟娬道“你真沒打他啊?”
Advertisement
殷珩目溫潤地看著,六畜無害道“他能跑能跳的,我腳不便、手無寸鐵,打不過他。”
孟娬覺得有道理,頓時就一陣張,道“你昨天怎麼不說呢,你要是被他欺負了怎麼辦?”
殷珩道“我沒被欺負,就沒說。”
過了一會兒,孟娬又問“那你知道他是被誰打的嗎?”
殷珩想了想,道“可能是摔了一跤。”
“剛好就摔斷了雙手?”
殷珩一本正經“摔在他買來的蓮子上,磕得比較重,剛好就摔斷了雙手。”
張氏氣沖沖地去到馮才那裡時,馮才才剛接回手臂,就聽張氏說要帶他去夏氏家裡和那個廢人對峙。
馮才在床角,死活不去。
不是他不肯,而是他不敢啊。
真要是去了,可能他就離死真不遠了。
他本想讓張氏去幫他討回公道,可他本人不出現,這公道也沒法兒討。最終隻能打落牙齒往肚子裡吞。
孟娬本來覺得那馮才自己摔斷了雙手這種事是不太有說服力的,可左等右等,也不見馮才來對峙理論。
要不是心虛,他會不來?
於是孟娬漸漸就信了,可能他真是運氣背到了極點,自己給摔的。然後他恰好又見殷珩在現場,便誣陷給他,想趁機訛一筆,結果失敗了。
這件事最後也就不了了之。
張氏卻是因此徹底和夏氏了惡。
夏氏想明白了張氏最開始的如意算盤,也沒打算再和繼續來往。
可後來,不知哪裡傳起的流言,就說夏氏年輕的時候定然是乾過見不得人的醃臢事,才生下孟娬這個兒。說不定孟娬就是不知和哪個野男人的私生,後熬不住別人的指指點點,才單獨搬到這裡的。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八卦,而且人們一向不吝去惡意揣測,彷彿隻有狠狠碾踩別人,自己心裡才能得到痛快。
Advertisement
夏氏素來在意這些,風言風語傳到了的耳朵裡,氣得哭了一場。
說來,孟娬和殷珩已經好幾天沒去街上表演了,孟娬都快忘了這回事了。
這時,幾個著普通布的年輕小夥子,正紮堆走在巷子裡。中間的一個手裡拿著一塊木牌,木牌上寫的是一個地址。
旁邊的人煩躁地撓撓頭,道“,大姐頭怎麼住這麼復雜的地方,這裡這麼多戶人,這個地址怎麼找!”
良田喜事:腹黑夫君如花
良田喜事:腹黑夫君如花
猜你喜歡
-
完結925 章
曆史專家穿越記
弘治十一年。 這是一個美好的清晨。 此時朱厚照初成年。 此時王守仁和唐伯虎磨刀霍霍,預備科舉。 此時小冰河期已經來臨,綿長的嚴寒肆虐著大地。 此時在南和伯府裡,地主家的傻兒子,南和伯的嫡傳繼承人方繼藩……開始了他沒羞沒躁的敗家人生。
230.9萬字8.18 300803 -
完結407 章

嫡女心計,傻王的心尖寵
前生的死,鑄造今生的她,無鹽容貌之下藏著驚為天人的資本,她浴火重生,準備給害死她的人點顏色看看。 什麼小三,什麼后媽,什麼渣男,統統閃一邊去,誒?你是誰家的傻子,敢攔我的路? 他,當朝最受寵的王爺,卻不料一夜之間成為傻子,變成帝都的笑柄,可是傻子樣貌的背后,卻藏著一顆狠辣的心,一直到遇到她,他發誓,此生非親不娶。 你問傻子干嘛?傻子找媳婦,相中了她......
101.5萬字8.18 71736 -
完結1088 章

不藏好馬甲就要繼承億萬家產
從星際穿越過來的AI喬蘊,成了豪門陸家丟失在鄉下的大小姐,十五年后出于某種目的終于回家了。 外人都以為這下鄉來的,又窮又酸,毫無文化,舉止粗魯,等著看她笑話,直到后來…… 陸大哥突然發現:他剛簽的合同居然是妹妹隨手送的?? 陸二哥震驚:什么!?我的大男主電影是妹妹投資的!! 陸媽媽:女兒送我的三無產品,是頂尖研究院出品的!? 陸爸爸:女兒送我的贗品,居然是價值千萬的真跡!? 各領域大佬齊齊發聲:來做老師嗎?年薪上億的那種? 某大集團怒而發聲∶玩夠了沒有?還不快回來繼承億萬家產。 渣渣們:說好的凄慘弱小可憐無助呢? * 厲寒洲在得知喬蘊和自己并肩首富的那天,立馬清算了財產,擺在喬蘊面前:“這些全部送給你,附送贈品老公一位!麻煩簽收。” 喬蘊:“你說過不準早戀,做人要守信用。” 厲爺∶#急!如何回到過去打死自己?# ——世界欠你的溫柔,我來補給你。
182.3萬字8.18 122853 -
完結506 章

媚婚之嫡女本色
陌桑穿越了,穿越到曆史上沒有記載的時空,職場上向來混得風生水起的白領精英,在這裏卻遇上讓她恨得咬牙切齒的克星,高冷男神——宮憫。 他嫌她為人太過陰詭狠毒。 她嫌他為人太過高冷孤傲。 本想無事可做時,虐虐渣女渣男,逗逗小鮮肉。 豈知一道聖旨,把兩個相互看不順眼的人捆綁在一起,組成嫌棄夫婦。 自此兩人過上相互猜測,彼此防備,暗裏算計,夜夜心驚肉跳的生活。 豈知世事難料,兩個相互嫌棄的人看著看著就順眼。 她說“你是護國賢臣,我是將門忠良,為何跟你在一起,總有種狼狽為奸的覺悟。” 他說“近墨者黑。” 陌桑點點頭,確實是如此。 隻是,到底是誰染黑誰啊? 再後來…… 她說“宮憫,你是不會笑,還是從來不笑?” 他看了她十息,展顏一笑“陌桑,若知道有一天我愛你勝過愛自己,一開始就不會浪費時間防備你、猜疑你,而是把所有的時間用來狠狠愛你,因為一輩子太短,我怕不夠愛你。” 陌桑咽著口水道“夫君,以後千萬別隨便笑,你一笑,人就變得好風騷……” 宮憫麵上黑,下一秒就露出一個魅惑眾生的笑容“娘子放心,為夫隻對你一人笑,隻對你一人風騷。” 某女瞬間流鼻血…… 【這就是一個白領精英穿越到異世古國,遇上高冷男神,被帝王捆綁在一起,相殺互撕,最後相親相愛、強強聯手、狼狽為奸的權謀愛情故事。】
187.7萬字8.18 335163 -
完結4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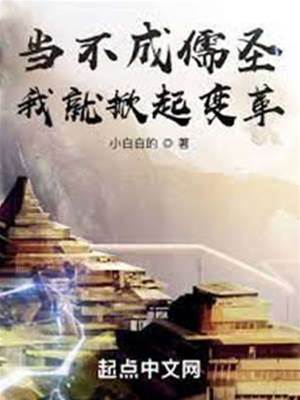
當不成儒圣我就掀起變革
作為一個演技高超的演員,林柯穿越到了大魏圣朝,成了禮部尚書之子。但他是娼籍賤庶!這個世界把人分為上三流,中流流,下九流……而娼籍屬于下九流,不能參加科舉。母親是何籍,子女就是何籍!什麼?三尊六道九流?三六九等?我等生來自由,誰敢高高在上!賤籍說書人是吧?我教你寫《贅婿兒》、《劍去》、《斗穿蒼穹》,看看那些個尊籍愛不愛看!賤籍娼是吧?我教你跳芭蕾舞、驚鴻舞、孔雀魚,看看那些個尊籍要不要買門票!賤籍行商是吧?你有沒有聽說過《論資本》、《論國富》、《管理學》、《營銷學》……還有賤籍盜,我和你說說劫富...
30.5萬字8.18 27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