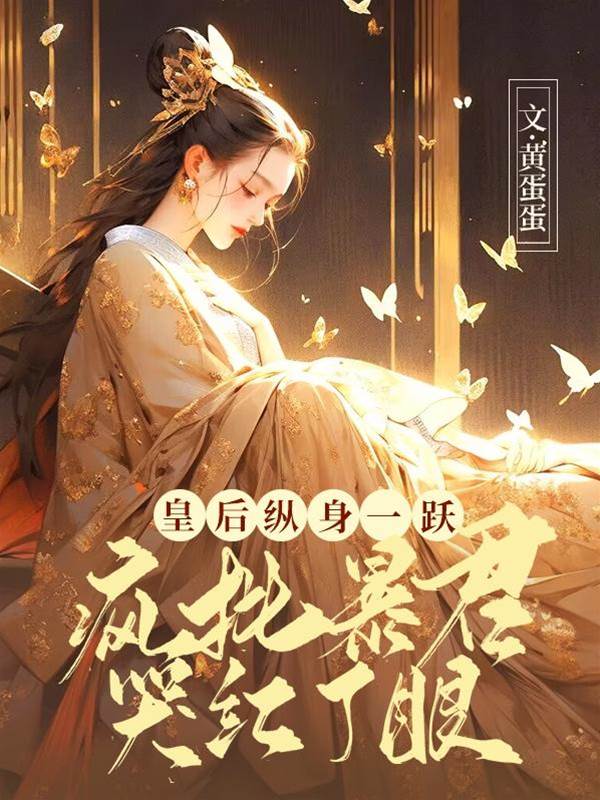《歡喜農家科舉記》 第137章 你希望誰是案首
何時同孟中亭有了,這事崔稚也說不清楚,搖了搖頭。
“大概有些緣分吧!我瞧著那孩子好的!”崔稚將一塊涼瓜遞給魏銘,“出門的時候,孟家灶上的大娘送我的。”
魏銘接過瓜,打量了一下,“像是西邊來的瓜,山東倒不常見。”
崔稚“呦”了一聲,“還是好東西呢!”
“可不是?”魏銘又把瓜遞了回去,“灶上的大娘未必能做這涼瓜的主。”
那就應該是孟中亭的意思了。
崔稚驚訝了一下,轉過頭看了一眼段萬全。段萬全正同人打招呼,不過顯然也聽見了這話,笑道:“孟案首向來大方。”
“嘖!”崔稚道:“那我還真是遇見貴人了。”
魏銘不置可否,繼續跟著大部隊往前走,又把涼瓜塞了回來,“我遇上貴人也不能了你的好,吃吧吃吧,天熱呢!”
涼瓜被捂出了幾分熱,也不知道揣了多久。
魏銘接過來,臉上出點點笑意,問,“你這幾日仍舊在孟家小宅住?可有不便?”
崔稚點頭又搖頭,“他已經搬回孟家去了,畢竟道試在即,他們家府邸更方便。他讓我和全哥等到道試結束再回去,我倆也不能辜負他的好意不是?”
魏銘瞧說著,過手來拍拍他的肩,“可惜不好把你也接過來住!”
倒還想著他魏銘不又將上下打量一番,目落到一簇新的柳黃鑲襽邊的上,不由問道:“難道裳也是孟家的?”
“怎可能?”崔稚哈哈笑起來,“我又不是嫁給孟中亭了,只是借住他家而已!”
突然說到了“嫁”,魏銘愣了一下,再見這副俏模樣,又回想起孟中亭上一世風無限的年月,忽然覺得竟有些相配。
Advertisement
只是孟家后來敗了,孟中亭的下場又格外地凄慘
他有心想提醒崔稚一句,再見早已忘卻了方才調笑的話,又說起了裳,“這一是清香樓的東家送我的,這清香樓的事兒吧,我得好好跟你說說。”
說著還指了指魏銘手上的涼瓜,“你吃瓜,我說給你聽!”
魏銘笑著點頭,吃著涼瓜聽說起了這幾日的事。
“我已經和殷杉說了,高矮生在道試等績那兩日往清香樓說書,到時候肯定場面火,鄔陶氏還不曉得氣啥樣!”
崔稚得意洋洋,魏銘聽了卻未出聲。
他這般姿態,崔稚一眼看去心里咯噔了一下,“怎麼?有什麼不妥嗎?”
魏銘側過頭看一眼,“你覺得鄔陶氏,會讓清香樓這般順利崛起?”
“那能如何?”崔稚挑眉,“還想用府手段不?”
“那倒不至于,或者說,在看到清香樓崛起之前不至于,”魏銘了一下眉心,“不過我以為,約莫還是會在高矮生上下功夫,畢竟高矮生才是和對抗的力量。”
這一點,崔稚自然思考過,渾不在意,“不就是想抓我嗎?我把高矮生的袍子一,能抓到線啊?”
這一招當然百試不爽,之前也有人想弄清楚高矮生的份,崔稚這邊只要換了行頭,沒有人能發現與高矮生的關系。
魏銘仍舊著眉心,“未必這般簡單,容我想想。”
他謹慎起來,崔稚原本坐等報復鄔陶氏抓之仇的心,也順著他定了定,“也是鄔陶氏不是個蠢人。”
待到了眾考生的下,崔稚已經同魏銘和段萬全假設了一堆,鄔陶氏可能對付高矮生和清香樓的辦法。
“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何況我們不是臭皮匠,鄔陶氏也不是諸葛亮!”崔稚把這些假設以及應對辦法全部都裝進了腦子里。
Advertisement
鄔陶氏想擺弄,且沒這麼容易!
天漸晚,明天眾考生休息一日,后日就是道試了。
走之前,崔稚小聲問魏銘,“你說你這一次,還能點案首嗎?”
魏銘反過來問,“你是想讓我中,還是不想?”
“這”
崔稚猶豫了一下,的答案并不是肯定而唯一的,魏銘學著崔稚平日的樣子攤了手,“看來你想讓孟中亭中案首。”
他說得的這麼肯定,崔稚反倒不肯定了。
“不能這麼說。我也希你能中案首,畢竟”
“畢竟什麼?”魏銘瞧著,夕下,長而的睫投出月牙一般的影。
“畢竟你連中小三元,我也跟著水漲船高,還能借機賺點小錢不是嗎?”崔稚大大方方說出了答案。
魏銘直接笑出聲來,“果然是為了賺錢!若不是為了賺錢,我看你希孟中亭能點案首。”
崔稚撇撇,輕聲喊他“魏大人”,“人家本來就是案首,被你的只能區居第二,我看著怪可憐的!”說著,朝魏銘眨眨眼,“要不,你給人家點機會!”
“為何要我給他機會?”魏銘道:“也許今歲能沖出旁的人點案首,也不好說。”
這話把崔稚說得一愣,接著目驚奇地打量魏銘,“魏大人,你好不講理!哪里還有旁人能點案首!這道試案首本來就是孟中亭的好不啦?”
魏銘面不改心不跳,“說到底,你還是要我給他讓位?”
崔稚就算再傻了吧唧,也聽出這話不太對勁,瞧瞧魏銘的臉,見魏銘雖然笑著,卻笑得不似平日里和氣,趕忙道:“我這不是隨便說說嗎?”
說著尤覺魏銘還是沒有出和善的信號,趕忙又道:“于,咱們倆是革命戰友,我和你住在一個屋檐下的時候可比跟他久多了!于理呢,魏大人是真才實學,點不中案首才奇怪呢!你說是不是呀,魏大人?”
Advertisement
話到最后,裝傻賣萌的聲音都出來了,還學著小乙平日的習慣,手撓了撓魏銘的手背。
魏銘就算是生氣,見這樣,氣也消了。何況魏銘并沒生氣,他被崔稚撓得手背發,含笑瞧了一眼。
“點誰做案首,是提學的事。”他道,“孟中亭未必不能點中。”
說完便也不再解釋,了段萬全一聲,見段萬全走過來,便道,“天不早了,盡快回去吧,小心路上不要被盯梢。”
段萬全自然曉得厲害,連聲應了,去崔稚離開,卻見眨著眼犯傻,“這會兒傻什麼?快走了。”
崔稚還在瞧著魏銘,瞧著魏銘不知何時已經比自己高出一頭,負手站在夕下,影子拉長到了樹下,真有幾分古裝劇里居高位大臣的覺。
尤其他方才說得話
說來說去的,到底是誰能點中案首呀?
崔稚又愣了一下。
自己本來就是問了他一個簡單的問題,看他給扯到哪里去了!偏偏扯了一圈又繞回了原點,到底沒說到底誰能點中案首!
崔稚覺得自己上了鬼子的當了!
被段萬全拉著走了幾步,才回過神來,忽的朝魏銘道:“明日不給你做夾饃帶著了!”
夕下,院中暖風吹起魏銘的擺,他笑出聲來,“也好。”
崔稚更震驚了。
他竟然說“也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021 章

華帳暖,皇上隆恩浩蕩
大計第一步,首先得找個結實的金大腿,可沒曾想抱錯了,紮臉,可否重抱? 隻是為何她重新抱誰,誰就倒了八輩子血黴?不是傾家蕩產,就是滿門抄斬? 好吧,她認,就算三王府是龍潭虎穴,她入,反正她有二寶。 一,讀心術,雖然,此術獨獨對卞驚寒失靈。 二,縮骨術,雖然,此術讓本是成人的她看起來像個小孩。 在三王府眾人的眼裡,他們的王爺卞驚寒也有二寶。 一,豎著走的聶絃音。 二,橫著走的聶絃音。 有人問聶絃音,三王爺對你如此好,你要怎麼報答他? 聶絃音想了想,認真說道:「我會把他當成我親爹一樣侍奉!」 直到那一日,有人當著他的麵,跟她說,等她長大了娶她,她點頭如搗蒜,卞驚寒便徹底撕破了臉,也撕了她的衣。 她哭得驚天動地:「你禽.獸,我還是個孩子。」 某男淡定穿衣,唇角一抹饜足微弧:「比本王小兩歲,的確算個孩子。」
154.6萬字8 34773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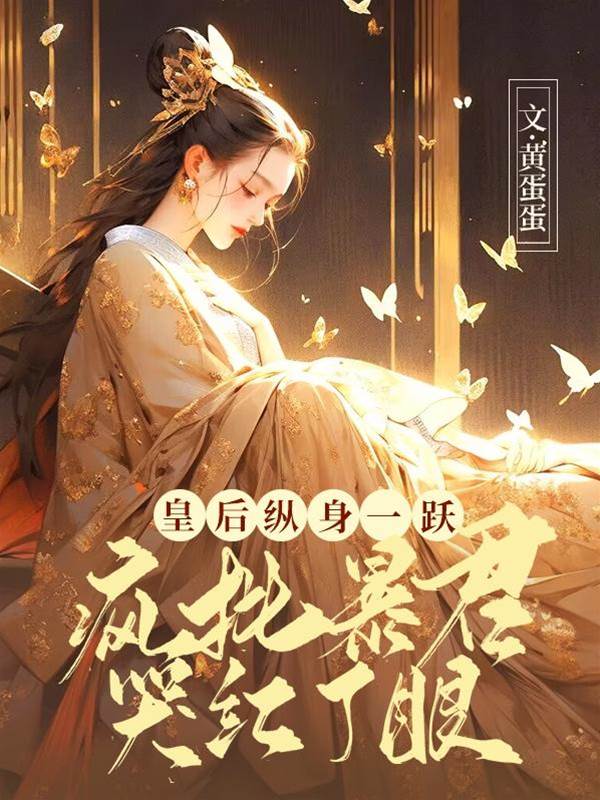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
完結31 章

惹春嬌
【冷情國公世子vs草包將門美人】【歡喜冤家 一見鍾情 奉子成婚 甜寵1V1sc】崔恪出身名門,大家公子,這輩子都沒想到自己會娶甄珠這樣一個女人。她出生鄉野,毫無學識,貪財好色,蠢笨粗俗。且與他是天生的不對付。第一次見麵,脫鞋甩在他臉上,還將他推下河引來重病一場。第二次交集,因賭錢涉案栽在他手上,罰她吃了幾天牢飯,臨走時把滿腹汙穢吐在他的衣裳。輪到第三次,一夜春宵後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懷上了他的崽崽……起初的崔恪:“要娶甄珠?我崔夢之這是倒了幾輩子血黴?”後來的崔恪:“娘子不要和離,夫君什麼都聽你的!
7.9萬字8.18 3744 -
完結436 章

繼妹非要和我換親
宋尋月繼母厭她,妹妹欺她,還被繼母故意嫁給個窮秀才。怎料沒多久,窮秀才居然翻身高中,后來更是權傾朝野。她一躍成為京中最受追捧的官夫人,一時風光無量。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這玩意背地里是個多麼陰狠毒辣的東西,害她心力交瘁,終至抑郁成疾,早早亡故。重生后,就在宋尋月絞盡腦汁想要退婚時,她同樣重生回來的繼妹,卻死活要和她換親。為了擺脫前夫,宋尋月咬牙上了郡王府的花轎。都說琰郡王謝堯臣,母妃不受寵,自己不上進,除了身份一無是處。可等真的嫁去郡王府,宋尋月才發現,謝堯臣居然這麼有錢!而且他還貪玩不回家!過慣苦日子的宋尋月,一邊品著八種食材熬制的鮑魚湯,一邊感動的直哭:家有萬金,府中唯她獨大,夫君還不愛她,這是什麼神仙日子?謝堯臣上輩子只想做個富貴閑人。怎知那蠢王妃借他之名奪嫡,害他被父皇厭棄,死于暗殺。重生后,謝堯臣備下一杯鴆酒,準備送蠢貨歸西。怎知蓋頭掀開,王妃竟是前世病逝的顧夫人。謝堯臣冷嗤,看來不必他動手。可時間一長,謝堯臣發現,他這個新王妃不僅身體康健,還使勁花他錢。每天吃喝玩樂,日子能過出花來。謝堯臣坐不住了,憑什麼娶回個王妃使勁花他錢他還守活寡,他是不是傻?于是在那個良夜,他終是進了宋尋月的房間。老皇帝當了一輩子明君,可上了年紀,兒子們卻斗得一個不剩。悲痛郁結之際,他那廢物兒子和王妃游歷回來了,還帶著個小孫子。一家三口紅光滿面,圍著他又是送禮物又是講游歷趣事。又感受到天倫之樂的老皇帝,輕嘆一聲,就把皇位送出去了。謝堯臣:?宋尋月:?在顧府悔恨難當的宋瑤月:???
70.6萬字8.18 55917 -
完結190 章

花好孕圓
从棺材里醒转,传说中的相公跟小妾在旁亲热,是躺回去呢,还是爬出来?——这是一红颜祸水不幸遇到个色中饿鬼的狗血故事。
56.7萬字8.18 27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