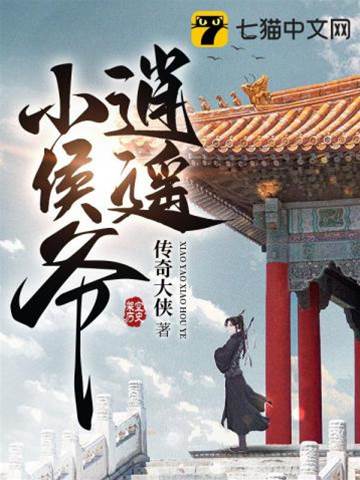《贅婿》 第二〇七章 家事
未時兩刻,就在依荷園中龍伯淵與丁宛君對坐閒聊之時,西湖之上,一艘畫舫正順碧波徜徉,緩緩而行。
這是專爲遊湖而造的舒適舫船,船隻一層,通緻,但並不顯得張揚,頂棚張開,寬而且厚,大概有兩三層的夾層,稍有隔熱功能。這時候天氣雖熱,但過了午後,湖上風大,船上薄幔輕紗,四面通風,船艙之中便只是涼爽的覺了。
午後、畫舫、西湖。若以西制的時間,不過是下午兩點左右,縱然寬敞的船艙並不熱,偶爾才能見到一兩點船影的寬敞湖面也足以帶來懨懨睡的氛圍。若有其它船隻從旁經過,應當也能發現,此時的船艙裡,畫舫的主人也已經在竹製的涼牀上睡著了,船艙裡桌椅都矮,一副擺了黑白棋子的棋秤安安靜靜地擱在艙室口旁,顯示出不久前還有人在這下棋的事實,下棋的大概是旁邊兩名丫鬟打扮的,此時兩人倚靠在船壁上也已經進夢鄉,一名摟住另一名的腰,將頭擱在了的肩膀上,被摟住的手中拿著一把扇子,偶爾卻還扇一下。
船艙另一側的窗口前,也有一名坐著矮凳,趴在前方的小桌上正目迷離地整理著手頭的事。大概是艙唯一清醒的一人,手中執著筆,正在前方看來像是賬冊的本子上理事,偶爾勾勒一筆,大抵不是什麼很重要的東西,勾勒一陣,也打著呵欠趴在桌上瞇一陣,隨後又強自打起神,迷迷糊糊地擡起頭來,一隻手託了下,另一隻手繼續翻。
炎炎夏曰,這畫舫間薄紗輕揚的悠閒一幕,足可畫。畫舫上自然也有掌船的船伕等人,但基本不會到這邊來打攪主家睡眠。再過得一陣,窗邊整理賬冊的丫鬟也終於支持不住,沉沉眠了。
Advertisement
不知什麼時候,約間,有影走了過來,將窗邊飛的薄紗紮起來,隨後拿了薄毯蓋在三名丫鬟的上。湖上畢竟風大,既然睡著了,也總得稍作預防。
原在整理賬冊的丫鬟稍稍睜開眼睛,迷離的目之中,拿到頎長的影正在船頭擺來扭去,是在做什麼名熱運的作,再過得片刻,只聽撲的一聲,那影扎進湖水裡。
或許是該起來了。丫鬟心中想著,但不久,視野的一側,也有另一道白的影走過去,那是主人的影,去到船頭,蹲在那兒整理了男主人下的外袍,隨後在船舷邊坐下,倚靠著船一側的欄桿,雖然已經醒了,但緒看來仍有些懨懨的。
風吹過,白的襬輕輕地飛舞起來,隨著幾縷因午睡而了束縛的髮悠然飛揚著。
約的說話聲在前方傳來,主人雙手抱著欄桿,搖了搖頭,縱然只是背影,也能看出主人心慵懶而愉悅,大概是姑爺又讓下水去玩了。
主人與姑爺之間的很令人羨慕,縱然作爲丫鬟的也見過了不大家族的事,但仍然未在其它任何地方見過有這種的夫妻,那不僅僅是和睦與相敬如賓可以形容的,在姑爺是贅夫婿的前提下,那甚至足以稱得上奇怪。每次這樣想起,名杏兒的丫鬟總忍不住想想自己往後的夫婿可能會是怎樣的一個樣子,若也能有這樣的覺,那便好了,如果不是,便不親,或許也是無妨的,反正自己一輩子也會在蘇家,小姐跟姑爺也對自己蠻好的。
自家況,比起其他大戶人家的況,是相對特殊的。是小姐手下的大丫鬟,通常況下,也會是通房丫鬟,可姑爺是贅的,會被安排給姑爺的可能便不高了。一般人家的小姐邊,也不會安排三個丫鬟,自家小姐是因爲後來在外面拋頭面,打理商事,因此多要了兩個。小姐跟姑爺好,如今小嬋跟姑爺之間大概是定下了,和娟兒倒是不清楚此後會怎樣。
Advertisement
以往倒是蠻清楚的。
似們這樣的,小姐在家中也有地位,往後無非是被許配給家中得力的下人或是掌櫃,本還是會在蘇家繼續當丫鬟。到時候們的夫婿在蘇家也被看好,們本也有地位,不會欺負,相對於其他的丫鬟,們是最容易過得幸福滿的一批。
誰的生活軌跡都差不多,犯不著多想,但這一兩年來,看到了更加更加好的一些事之後,心中反倒是有些空虛起來。往後的那個著落,似乎忽然就變得不算有著落了。
小姐是等到很晚才的親,不過與娟兒的年紀,如今也已經大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被小姐過去說起這些事,不知道娟兒有沒有想過,但最近倒是偶爾會想想這些事。
小姐既然已經起來,也沒辦法再睡下去,但前方那樣的氣氛,也不好就這樣起來,便趴在這裡,瞇了眼睛看著。又過得許久,大概已至申時,下午的天變得明顯起來,姑爺從湖裡上來了,去到側面的艙室裡換服,那邊抱在一起睡著的嬋兒與娟兒也已經醒來,丫鬟們去後方準備銀耳蓮子羹,又拿了裝有冰塊的箱子,從裡面敲下冰粒來,船艙之中,方纔變得熱鬧起來。
月餘時間以來,一家人常常會在西湖上游一下午。
這時候通和信息都不算髮達,一個地方的商界,地域姓與排他姓終究比後世要強得多。寧毅陪同著妻子拜訪一商家,通常都是選在上午。從行首龍伯淵開始,基本每天都會有安排,當然,拜訪過後,便相對自由一點,若不是有什麼必要的事,通常都會找地方遊覽消暑。
都是一家人,無需打點應酬,自然可以更隨姓一些,試過幾地方之後,蘇檀兒便花了錢買下一艘畫舫,偶爾從別人家中出來,便直接上了船,在船上吃午飯,然後睡個午覺,下午便自行打發,聊天下棋,討論商場上的決策。如今寧毅與蘇檀兒所接的信息都差不多,話題倒也蠻多的,他在別人家中向來保持沉默,倒是在只有夫妻兩人時,會談論一下今天拜訪後的看法,對方的態度如何,該送些什麼樣的禮品,往後怎樣等等,如此一來,倒也促了幾筆小的合作生意。
Advertisement
只是初到杭州,大的生意暫時是很難做的,在這等有排他姓的市場裡,寧毅與蘇檀兒的想法,也不過是籍著幾個月的時間讓大家瞭解“我來了”、“市場多了一個商家,但我們與其它商家也並沒有不一樣”,等到大夥兒多適應了,纔是真正要大刀闊斧推廣江寧布藝的時候。
相對來說,包括買畫舫、買住的宅院,以及其它各種遊覽花的錢,倒已經比初期的商業投資更多了,不過,初期只是些小錢,蘇檀兒倒也並不介意。
與寧毅這夫婿玩得開心悠然,在各種事上,也頗爲相諧,令見了的人都不爲之羨慕。如今在姐姐的力下暫時收了姓子幫忙做事的文定文方偶爾也會來畫舫上度過一個下午,寧毅便找了他們下船游泳。
說起游泳,蘇檀兒本其實是有些反對的,時代如此,有家有業有份的人,在公衆場合做這種事的終究讓人覺得不太好。蘇文定蘇文方也是這樣的想法,但寧毅聽說他們會遊,便一腳一個將兩人都踢了下去,蘇檀兒對此便也沒什麼辦法,何況本也被寧毅折騰過下了一次水,只要周圍沒什麼遊船,對於寧毅游泳的嗜好,也只好聽之任之了。
那次下水,自然不會是出自自願,當然,也不是兩個弟弟那樣被寧毅一腳踢下。當時寧毅已經鍛鍊過數次,記憶中的水姓漸漸恢復,他跟蘇檀兒說了幾次下水試試蘇檀兒都不肯,就算拿商場上的事來打賭對方也絕不拿此事來賭。當時寧毅下水只一會兒,心中想想,忽然做出往下沉的模樣,撲騰幾下,說是筋了。畫舫上方船伕、夥計都不在視野中,當時只有蘇檀兒在,只見驚愕地愣了一愣,便就那樣穿著跳下來了。
Advertisement
只是小時候遊過泳,說是會遊,其實水姓也有限,著急之下,差點把自己也淹著,嗆了好幾口水,被寧毅攬住之後才知道被騙。看著寧毅一臉寒冰,儼然已經是在手下夥計面前罕見發飆時纔會有的嚴厲面孔,寧毅捧住的臉親住,也是拼命掙扎。
蘇檀兒本是個姓與主見都極強的子,在寧毅面前溫婉是因爲教養,這時候心起伏,一般的安本糊弄不了,後來便想上船,卻仍然被寧毅拖著在水裡遊了幾圈,初時掙扎幾下,後來便逆來順了。到上了船,便板著臉一直安靜,將嬋兒娟兒們都給嚇到了,如此一直到晚上,洗漱完畢後板了臉在桌前理賬冊,不肯上牀,寧毅便過去,那邊打開一本,這邊便拿走一本,直到蘇檀兒目冷冷地瞥著他要發作,他才說道:“睡覺了。”
“不睡……”蘇檀兒直著脖子,一字一頓地說話,話還沒說完,被寧毅扔到牀上,隨後,兩人便廝打起來。
三個丫鬟在外面聽得心驚跳的,嬋兒急得兩隻手都已經了拳頭,好在蘇檀兒也沒有大喊大讓旁人進去什麼的。過得片刻,房間裡才安靜下來,三人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房間裡的牀上,蘇檀兒被寧毅用左手按住雙手手腕,在下,卻是一口咬在了寧毅的右手手臂上,這一口咬得頗重,滲出來,的目在下方直勾勾地瞪著寧毅。
寧毅任咬著,過得片刻,說道:“母老虎。”
蘇檀兒恨碎了銀牙,口中再次用力,再度滲出來。寧毅倒是眉都不一下,兩人就這樣互瞪了半晌,寧毅笑著俯下子:“我認識一個馴虎的人,他的手上全是被咬被抓的印子,可見幹這行總是要被咬的。”說著在蘇檀兒眼睛上親了一下,蘇檀兒原本眼睛瞪著,間他俯下來,只好閉上,倍屈辱,原本還想用力咬,但脣間已經嚐到腥甜味,不覺鬆了口,咬牙道:“你放開,你出去!”
“不放。”
“你這個……你這個……”
“贅的?”
“……”蘇檀兒原本恨恨地不知道該罵什麼纔好,這時候臉卻陡然白了,看著寧毅的臉,目中緒紛,不知道該怎樣說:“我、我沒……”
外面在聽窗戶的三個丫鬟約聽見“贅”兩個字,臉也白了,蘇檀兒與寧毅親兩年,這算是第一次吵架,但三個丫鬟都明白,吵什麼都可以,但如果吵到這個詞上,那後果就不堪收拾了。
蘇檀兒也不清楚自己方纔的緒有沒有挪到這上面來,看著寧毅的笑臉,心底都涼了下來。不過就算經歷過這麼多的商場來往,一時間也沒辦法分清寧毅此時的緒到底是怎樣,寧毅笑了笑,仍不放開:“沒有用的,我還是不放。”他將正在流的右手撐在蘇檀兒的邊。
“我……你……”蘇檀兒抿了抿雙脣,“我……我沒說那個……”
“說也沒用,反正你是嫁給我了……不贅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你家裡人也許覺得有,外面的人也許也會覺得有,可實際上沒有,不管我怎麼娶到你的,最後都是一樣的事。我如果真想做什麼事,沒幾個人擋得住,江寧的那些人擋不住,杭州的這些也擋不住,烏家的那些人擋不住,岳父、爺爺他們也擋不住……有些事我不做,只是因爲我真的不想做而已。”
寧毅在耳邊輕聲說著話,沒有太過強調的語氣:“今天你跳下來,我很……你是我娘子,並不是因爲我贅到了你們蘇家。”
蘇檀兒臉瞬息萬變,窘迫道:“你、你說什麼呢……”
“沒什麼啊,只是想告訴你,我今天很,因爲你想也不想就跳下來了。我的時候,你卻要發脾氣,這很不應該,明明你後來也遊得很高興的,卻一直要板著臉……”
“我、我沒有……你放開我……”
“哦,還有,我要告訴你,男子漢大丈夫,說不放就不放……”
說話間,蘇檀兒還要掙扎,陡然間到下的靜,杏目一圓,臉上陡然紅起來。
“你你你……你不能……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刺激啊……”
“你手上還在流呢……”幾乎要哭出來了。
這個晚上過了許久,蘇檀兒才能爲寧毅包紮好手臂上的傷口。當兩人躺在牀上準備真的睡下時,蘇檀兒回憶一番,才記起自己是被對方顧左右而言他,繞歪了主題。
“寧立恆,我還沒說,我今天很生氣……”
“但是都表現出來了啊。”
“你沒有道歉……”
“……”寧毅沉默半晌,手攬住妻子,嘆了口氣,“那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錯了也不會道歉的。”
“……你無賴。”
“其實下次你可以問我爲什麼要贅。”
蘇檀兒了一:“爲什麼啊?”
“忘記了,你忘了我失憶過?”
“……”方沉默,“你放開我。”
“嗯?”
www•ttκǎ n•C〇
“我要背對著你睡……”
於是在寧毅懷裡背對著他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寧毅問起跳下去時的心時,倒是什麼都不肯說了,其實自己也記不起當時的心了,許是沒有什麼心,就那樣跳下去了,只是這些事,也是不可能跟寧毅說的。
其實兩個月的時間以來,自從知道秦嗣源上京之時曾經邀請過寧毅,蘇檀兒的心中老是覺得矛盾和複雜。這一個多月來,又是寧毅陪了一家家的拜訪,對方知道寧毅乃是贅的夫婿之後,總是難免有各種目,就算多明白寧毅的不介意,心中也不免產生各種想法,特別是在六月間秦嗣源已經位居右相的消息傳來,關於贅二字,在心中也已經變得愈發敏。
倒是在這件爭吵之後,心中的某些緒,才稍稍的平靜下來。只是此後寧毅要下船游泳,有時候也讓下去,反正左右無人,寧毅並不介意自己的家人做些運,但蘇檀兒已經是打死也不下水了,只是對於自家相公一個人下水多有些擔心,一旦寧毅下去,便坐在船舷上看著,有時候寧毅過來,在船舷邊的水裡與說話,便讓了鞋,將雙足浸水裡。其實這年代許多子對雙足的自矜甚於,若遠遠看見有船過來,便立刻將雙足收上來,籠在襬裡,悄悄將鞋穿上。
此時雖然來了杭州已有月餘,但除了每曰裡例行的一番走訪,夫妻兩人其實還只是在自己的這片天地裡生活著,只偶爾與樓舒婉有些來往,也與樓舒婉的兩位哥哥樓書恆樓書見過幾面,偶爾在黃昏回家時,寧毅會在路口看看那劉氏武館中一幫壯漢嘿嘿哈哈地打拳,這時夕從樹隙灑下來,小嬋或是其他的家人跟在他的邊,曰子倒是是一派悠閒有趣。
到得六月中旬過後,方纔有一名陌生人過府拜訪,這人卻是與錢希文有關,名時昌頎,因爲聽了寧毅的名字,過來拜會,只是待到知道寧毅贅婿份之後,似乎就從目瞪口呆變過府申討了……
(未完待續)
猜你喜歡
-
完結387 章
腹黑毒女神醫相公
冬暖故坐著黑道第一家族的第一把交椅,沒想過她會死在她隻手撐起的勢力中.也罷,前世過得太累,既得重活一世,今生,她只求歲月靜好.可,今生就算她變成一個啞巴,竟還是有人見不得她安寧.既然如此,就別怨她出手無情,誰死誰活,幹她何事?只是,這座庭院實在沒有安寧,換一處吧.彼時,正值皇上爲羿王世子選親,帝都內所有官家適齡女兒紛紛稱病,只求自己不被皇上挑中.只因,沒有人願意嫁給一個身殘病弱還不能行人事的男人守活寡,就算他是世子爺.彼時,冬暖故淺笑吟吟地走出來,寫道:"我嫁."喜堂之上,拜堂之前,他當著衆賓客的面扯下她頭上的喜帕,面無表情道:"這樣,你依然願嫁?"冬暖故看著由人攙扶著的他,再看他空蕩蕩的右邊袖管,不驚不詫,只微微一笑,拉過他的左手,在他左手手心寫下,"爲何不願?"他將喜帕重新蓋回她頭上,淡淡道:"好,繼續."*世人只知她是相府見不得光的私生女,卻不知她是連太醫院都求之不得的"毒蛇之女".世人只知他是身殘體弱的羿王府世子,卻不知他是連王上都禮讓三分的神醫"詭公子".*冬暖故: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欺他辱他者,我必讓你們體會
149.1萬字8.18 75123 -
連載617 章
大唐醫王
一個現代醫師回到貞觀年間,他能做些什麼?如果他正好還成爲了李淵的兒子,李世民的弟弟呢?李元嘉,大唐醫王。
117.4萬字8 29994 -
完結195 章
嗜寵夜王狂妃
世人皆傳:“相府嫡女,醜陋無鹽,懦弱無能”“她不但克父克母,還是個剋夫的不祥之人”“她一無是處,是凌家的廢物”但又有誰知道,一朝穿越,她成了藏得最深的那個!琴棋書畫無一不通,傾城容顏,絕世武藝,腹黑無恥,我行我素。他是帝國的絕世王爺,姿容無雙,天生異瞳,冷血絕情,翻手雲覆手雨,卻寵她入骨,愛
74.8萬字7.92 52514 -
完結8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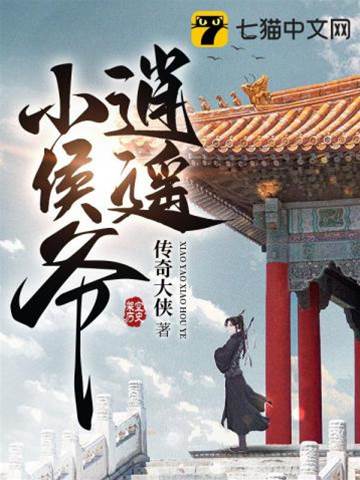
逍遙小侯爺
穿越古代,成了敗家大少。手握現代知識,背靠五千年文明的他。意外帶著王朝走上崛起之路!于是,他敗出了家財萬貫!敗出了盛世昌隆!敗了個青史留名,萬民傳頌!
148.9萬字8 98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