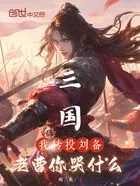《伐清》 第30節 賽跑
蔣國柱從來沒有想過要立刻揭發檢舉張朝與鄧名勾結一事,這種事不但難以說清,而且還會引起朝廷不好的聯想,畢竟蔣國柱和樑化也有不乾淨的往事。而且這件事還會牽扯到湖廣總督張長庚,江西巡已經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對手了,湖廣總督更是一個太過強大的敵人,現在蔣國柱還只是代理兩江總督,招惹不起這麼厲害的人。
而且蔣國柱還盼著有一天能爲正式的兩江總督,那時更需要和張長庚保持良好的關係,湖廣總督這樣有利的同盟不但對他的仕途大有益,同時也能幫他抵擋來自虁東的狂風暴雨——只要一天武昌還在張長庚手中,他就不需要面對鄧名的全部力。
除非面對鄧名這支老虎,否則兩江總督和湖廣總督不存在競爭關係,和張長庚爭鬥沒有任何益——就是扳倒了張長庚朝廷也不會讓蔣國柱兼任湖廣總督;而爲了更好的躲避老虎,蔣國柱也需要張長庚這個同伴,必要時還得拉他一把,不然若是同伴都被老虎吃了,那下次就得自己和老虎賽跑了。之前蔣國柱已經要求樑化站在江南提督的高度看問題,他本人當然也要站在兩江總督的高度縱覽全局,蔣國柱的政敵只是兩江境的競爭者。
“那時張朝的表一定會非常有趣,而我能親眼目睹,而那個滿肚子壞水的董衛國呢,也會痛悔不及,他也不想想,他憑什麼和我耍心眼?要是玩不過他,怎麼會我是代理兩江總督,而他只是一個小小的布政使呢?”蔣國柱在心中無地嘲笑著董衛國,覺得對方簡直就是魯班門前弄大斧,而憾則是因爲他無法真的實現這個計劃,因爲這裡還有一個討厭的障礙。
Advertisement
這個障礙就是右布政使朱國治,此人本是明朝的一個貢生,清軍南下後投靠滿清,在協助清軍鎮漢人反抗上不餘力,因此一路運亨通、青雲直上。郎廷佐出任江西巡時,朱國治就是他的心腹員之一,並因爲厲行保甲、搜捕抗清志士、殘酷剝削百姓爲滿清聚斂軍費等功績擡旗籍,爲八旗一員,是滿清統治者眼中的準自己人。
在鄧名原先的世界裡,鄭功取得的鎮江大捷導致蔣國柱在其退兵後被清廷抄家免職,接任江寧巡一職的就是朱國治。在得到這個重要職務後,朱國治立刻開始在江南推行全新的政策,嚴厲鎮對清廷的不滿言論,即使是對貪污員的控訴,也會被朱國治視爲危險的苗頭,上升到企圖背叛朝廷的高度,順治十八年的哭廟案中,朱國治包庇貪污的縣令,對舉報者進行無地屠殺,過程基本就是後來更大規模文字獄的預演和彩排。
在江蘇、在浙江、在雲南,朱國治死心塌地的爲清廷從事聚斂,對疑似反清的言論和思想則毫不猶豫地殘酷鎮,明目張膽地收賄賂,肆無忌憚地剋扣軍餉,在民間獲得了“朱白地”的稱號,就是朱國治在場中的同僚,也在背後用這個雅號來稱呼他。但朱國治得到了滿清統治者的青睞,對他腥鎮漢人的行爲表示了極大的讚賞,無論是索尼、鰲拜這樣的攝政大臣,還是親政後的玄燁,對朱國治都是恩寵有加。吳三桂起兵後將朱國治死,痛恨他骨的周軍士兵將其分而食之,骨無存。
朱國治這種對與漢人反抗者不共戴天的深深了玄燁,爲了表彰他對清廷死而後已的忠誠,清廷爲其著書立傳,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全天下宣傳他的事蹟,上升到了忠良楷模的高度。清朝滅亡後,對朱國治偉大的頌揚並未停止而是繼續延續,由一些漢人編寫的《清史稿》中,朱國治也是以聖賢面貌出現的;在電視劇《康熙大帝》中,朱國治一正氣、兩袖清風,吳三桂起兵時,用很長一段的朱國治與妻子對答的劇,來昭顯他爲國無暇謀的高尚,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朱國治義正辭嚴地拒絕吳三桂的勸降,痛斥其分裂祖國的反行爲,向周軍兵高呼滿漢平等口號,慷慨就義、含笑而逝。
Advertisement
在這個世界,郎廷佐在收到朝廷下達的追究鎮江戰敗之責、將蔣國柱革職抄家、管效忠發配爲奴的旨後,同樣立刻將朱國治從江西調來,準備向朝廷保舉他爲江寧巡。可這個世界的發展軌跡有所不同,朱國治還沒有趕到南京,戰局就又一次發生大變,鄧名生擒郎廷佐,全殲南京城下的清軍水陸兩軍,而朱國治也因爲通隔絕而不得不在池州府境停留。
等鄧名撤兵,朱國治能夠重新上路時,南京已是翻天覆地,郎廷佐叛國被殺,力挽狂瀾的蔣國柱以江寧巡的份代理總督衙門,並且與新任江南提督樑化結了同盟——遠在江西的董衛國認定兩人間必有間隙,一開始朱國治也曾這樣想,認爲蔣國柱和樑化以前的矛盾無法緩和、化解,但幾次試探後他卻驚訝地發現,因爲某些不爲人所知的原因,樑化與蔣國柱的同盟關係異常穩固,可以用牢不可破來形容。
對於這個來取代自己職務、郎廷佐的心腹,蔣國柱當然不會有任何好,而且他知道朱國治同樣是自己的競爭者,雖然沒有張朝的威脅那麼大,但同樣在朝廷的兩江總督候選人名單上;而朱國治不但對兩江總督這個位置有說覬覦,還深知若是蔣國柱得意,那自己的仕途就會變得一片灰暗,如果自己無法登上總督寶座,那朱國治寧可幫助張朝獲勝也不願意看到蔣國柱在兩江呼風喚雨。
儘管蔣國柱把朱國治視爲眼中釘、中刺,但也不能把他怎麼樣,因爲他知道這時朝廷的平衡之,朱國治就是用來督促他努力爲北京效勞、同時也是監視他的工。因爲深知朱國治不會在總督之爭中站在自己一邊,蔣國柱也不會向他任何,尤其是與張朝勾心鬥角的這些,若是告訴了朱國治那就與告訴張朝無異。
Advertisement
蔣國柱不願意讓朱國治呆在江寧這個要害之地,正好安慶知府把城池丟失過,還曾被鄧名俘虜,蔣國柱就讓朱國治去安慶以布政使份視知府事。漕運開始後,蔣國柱一度想調朱國治去協助漕運總督——這個協助工作從來都是吃力不討好,有了績是漕運總督的,若是除了紕則會爲漕運總督衙門的替罪羊。
可再三考慮後,蔣國柱卻是不敢。萬一朱國治做出了什麼績怎麼辦?或是朱國治用貪污來的錢財行賄漕運總督,攀上了關係,這豈不是給朱國治增加競爭兩江總督一職的籌碼嗎?再說,就算朱國治沒有辦法給自己創造機會,他破罐子破摔地搞破壞,變相替張朝出力又該如何是好?蔣國柱不敢說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反倒覺得可能很大——若是朱國治功地用漕運把蔣國柱拖下馬,張朝得志後一定會願意報答他的
最後蔣國柱不得不派了自己的一個心腹去協助漕運總督,千叮嚀、萬囑咐,讓這個心腹一定把事辦好,不要給蔣國柱的政敵任何機會。沒關係,反正等爲兩江總督後,收拾朱國治的機會多得很,不必急於眼前一時。
鄧名侵江西后,江蘇、安徽的力量紛紛向安慶集結,朱國治手中的權利突然急劇膨脹。不過蔣國柱以前並不曾放在心上,先期派去安慶的都是郎廷佐的殘存勢力,若是鄧名大軍突然抵達,正好用做消耗明軍銳氣的炮灰。
後來陸續抵達的部隊就不是朱國治能夠控制的兵馬了,這些綠營雖然稱不上蔣國柱的嫡系,但只會聽從兩江總督的命令。按照蔣國柱原先的時間表,接下來派去安慶的就會使由可靠同盟樑化統帥的兩江綠營銳,等樑化抵達安慶後,制朱國治不在話下,一點兒功勞也不會分給他。
Advertisement
只是現在計劃有變,鄧名實力強大,在完全沒有水師的況下,把他堵截在兩江境外本不可能,囤集重兵於安慶無異於放棄地。在沒有長江控制權的況下想確保各個重要城市,勢必要分散銳於各個要害城市,樑化也不能趕赴安慶。
“這次若是沒有朱國治在,我大可施展我的計劃,把張朝絕境。”蔣國柱苦苦尋找著最佳對策,到事變得有點麻煩,有朱國治這個定時炸彈在,蔣國柱當然不敢離開江寧去江西,而如果把朱國治放在外面,他就可能看出破綻,然後不顧一切地向朝廷舉報——如果蔣國柱取勝,朱國治的前途就會變得很糟,現在朱國治已經接近一無所有了,蔣國柱必須要防備他狗急跳牆:“算了,現在寧可把他放在江寧城裡,也不要讓他在外面給我添。”
如果把朱國治調回江寧,雖然會在蔣國柱試圖與鄧名取得默契時造一些麻煩,但是他覺得只要小心一些可以彌補,而且還可以由領兵在外的盟友樑化代勞。
很快蔣國柱就拿定主意,他依舊坐鎮南京,讓樑化前往揚州保護漕運不擾,同時分派一些兵馬協助地方部隊確保安慶、蘇州等府城,若是鄧名在長江上來回遊那也只好由他,只要保住這些關鍵城市、不發生大敗、漕運不被切斷的話,那蔣國柱就穩穩地跑在張朝前頭,和張長庚不分伯仲。
……
在拿到董衛國送來的頭一半贖城費後,鄧名立刻把九江還給他,這批又是在江西市價高達三十萬兩白銀的貨,剩下三十萬鄧名錶示可以等他返回路過九江時再給。而董衛國更代表張朝暗示,如果鄧名取得大勝,江西還可以提供一批額外的貨。
“怎麼覺我們像是他們的打手一般?”在前往安慶的中途,任堂突然冒出這樣一句話來。
“嗯,兵戰死疆場,收益的不是我們的國家,也有國家的敵人,這種覺確實很不好。”鄧名輕嘆一聲:“或許我們只能自我安,就當敵人願意替我們陣亡的將士承擔一部分卹吧。”
“這次提督不打算髮布檄文嗎?”任堂又好氣地問道。
“發佈什麼檄文?”鄧名一貫不喜歡發佈檄文,首要原因就是他的文言文寫作能力很差,邊也沒有幾個擅長此道的幕僚,其次鄧名還覺得這種檄文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一般百姓看不懂;經過這些年的摧殘,縉紳對滿清的畏懼已經深骨髓,如果明軍不展示出足以驅逐清軍的實力,縉紳本不敢投效過來:“再說發檄文後,若是真有士人率領族人來投軍又該怎麼辦?你也知道我們本不會在江南久呆的。”
“可發佈檄文不僅僅是一種號召,也是讓天下人明白提督驅逐韃虜、復兩京的志向,如果提督擔心有縉紳來投靠而又無法保護他們的話,提督完全可以不在檄文中號召他們來投好了。”上次鄧名來江南時只帶了很量的一點人馬,冒名頂替地潛兩江境,當然不可能發生麼檄文,而且鄭功和張煌言曾聯合發過一份檄文,鄧名就算不發也沒有大礙:“聽說提督上次討伐湖廣的時候都曾發過一封,江南這裡人文薈萃,爲何反倒無一言贈與江南士人呢?”
“上次我在湖廣發的檄文,只是爲了吹噓了一下我統帥的五十七萬的大軍。”鄧名聽得笑起來,那封檄文從嚴格意義上講並非政治宣言,因爲其中沒有明確提到出兵的目的,沒有對反正兵的待遇保證,本質上就是鄧名想和湖廣縉紳混個臉,讓他們對自己有個印象:“好像也沒有那個縉紳是因爲我的檄文而來通風報信的,胡全才在武昌的橫徵暴斂絕對比我的檄文作用大。”
“但終歸是一篇給湖廣父老的文字,”任堂仍然不肯放棄,固執地勸說道:“提督第二次來到江南,卻依舊惜墨如金,不一字給江南,難道提督也是流寇嗎?只有流竄的盜匪才悶頭犯案,唯恐別人知道自己的份和行蹤。”
“本質上我就是來流竄作案的,綁票、壟斷生意,砸競爭對手的場子。”鄧名在心裡說道,不過他當然不會把這話明確地說出來,他仔細琢磨了一下,也覺得任堂說的確實有其道理。
“向天下人表示我們與韃虜不共戴天決心的最好方式,莫過於我前去北京,親手向城門扔一長矛,或是一箭。”把另外幾個心腹軍召集來商議此事時,鄧名首先向他們解釋此舉的政治意義。
經過一番斟酌,鄧名同意任堂的說法,隨著實力不斷膨脹,他確實需要向天下人表示出自己與虜廷不共戴天的氣勢來。如果能夠進抵北京城下,仿效漢尼拔的樣子親自向北京城門投擲一長矛,鄧名確信會是非常完的政治表態,不過京畿地區滿清重兵雲集,鄧名覺得去哪裡風險太大,單純爲了投擲一長矛更是得不償失;而若是去廣東和福建投擲長矛很難說清到底是和虜廷勢不兩立還是和尚可喜、耿繼茂誓不兩立,再說三藩所部銳,一點兒也不比京畿的滿清軍隊好對付,何況那裡地理複雜,位置偏僻,信息傳達不暢,總之就是投資、收益更加地不比例,相比之下任堂的辦法確實是最可行的。
很快大家就都同意發檄文的建議,至於鄧名提出的,在檄文中不談此次出征的目的、不要求士人投靠種種,任堂也沒有表示反對。
“吾有十勝,賊有十敗!”這是任堂出的題目,鄧名覺得這個題目很好,足以向天下人表現出自己和滿清不死不休的決心,而且還可以宣傳一下自己的長,指出敵人必然失敗的遠景。再說十勝十敗論可是赫赫有名,三國演義裡就有,很多百姓雖然不識字,但是可能因爲喜歡評書而聽說過郭嘉的這段名言。
周開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立刻表示贊同:“這個題目不錯,很吉利。”他認爲吉利的原因就是因爲曹最後取勝了,而袁紹果然失敗了。
但也有反對的聲音,穆譚就嘀咕了一句:“提督可不是曹。”
“誰說提督是曹了?你不要瞎聯想。”任堂大聲地爲這個題目辯護,作爲這個題目的建議者,他對這個題目非常滿意,十勝十敗可是郭嘉的名作,雖然上次沒有功地說服鄧名同意他留下防守荊州,但扮演不曾諸葛扮演郭嘉也不錯。江南士子如雲,若是這篇檄文大熱,人人都知道是他任堂想出的這個題目,那豈不是豪傑仰慕、名士讚歎,更會把他任堂和郭嘉聯繫起來——雖然容不盡相同,但都是高瞻遠矚的十勝十敗論。
猜你喜歡
-
完結626 章

我,開局輔佐嬴政,成為六國公敵
張赫穿越大秦,獲得最強輔助系統,只要輔助嬴政,便能獲得十連抽。于是張赫踏上了出使六國的道路,咆哮六國朝堂,呵斥韓王,劍指趙王,忽悠楚王,挑撥齊王,設計燕王,陽謀魏王。在張赫的配合下,大秦的鐵騎踏破六國,一統中原。諸子百家痛恨的不是嬴政,六國貴族痛恨的不是嬴政,荊軻刺殺的也不是嬴政。嬴政:“張卿果然是忠誠,一己擔下了所有。”張赫拿出了地球儀:“大王請看……”
122.8萬字8 11384 -
連載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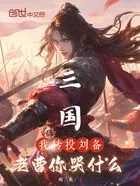
三國:我轉投劉備,老曹你哭什麼
秦瑱穿越三國,成了一個寒門士子。 為了改變命運,四處求學,最終投入曹操麾下。 憑著超越時代的見識,屢次建功。 本想輔佐曹操成就霸業,沒想到卻因功勞太大,引起曹操忌憚。 正逢宛城之戰,眼見老曹要一炮害三賢,秦瑱再次勸誡,卻惹得曹操怒斥。 於是秦瑱果斷掛印而去,你老曹不是多疑嗎?那這軍師不當也罷! 至此,秦瑱轉入劉備麾下,以一人之力,提前改變天下大局。 奪淮南、戰呂布、敗孫策、取荊州,短短數年之間,輔佐老劉成就霸業。 多年之後,曹操遲暮,病榻之前,謂眾人云: 「孤一生行事,但無悔過,唯秦子瑄離去,孤之過也」
118.5萬字8 33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