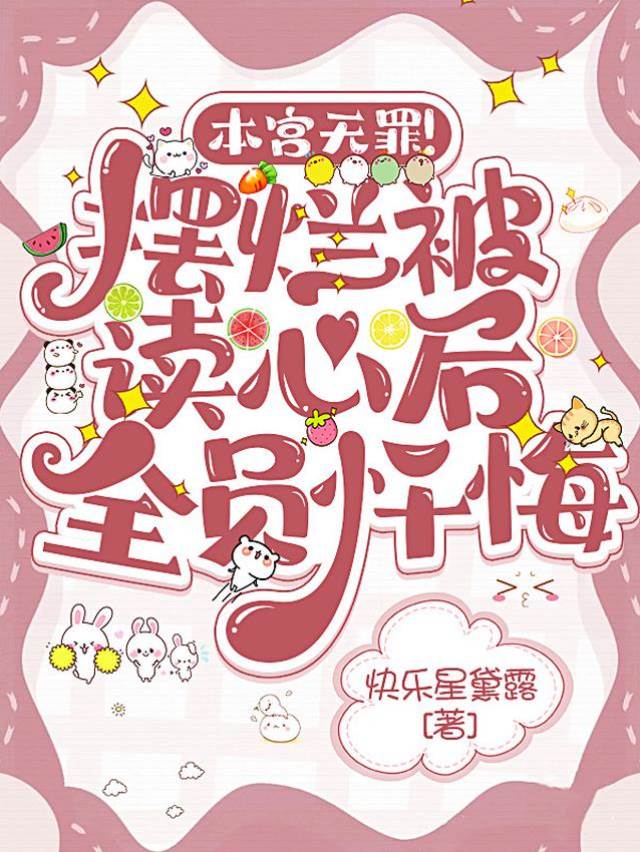《嬌妻如蕓》 第三十四章 姚氏封后
朝堂上,欽天監的王大人朝著袁崇武拜了下去,口中道:“啟稟皇上,臣昨日夜觀天象,發現天現奇觀,二十四星宿約有變,顯是紫微星有下凡之兆。”
他這一語言畢,朝堂上便傳來一陣竊竊私語,紫微星乃“帝星”,命宮紫微之星的人俱是帝王之相。此言一出,頓時有人出聲反駁:“王大人此言差矣,紫微乃是帝星,若紫微星下凡,難不是說咱大梁會有兩個皇帝?”
那王大人面不變,道:“非也,此帝星為輔,臣觀測良久,見此星約映照在宮中東南角,臣后來得知,那里乃是姚妃娘娘所居的玉芙宮,而姚娘娘不日便要分娩,若娘娘生產之時,便是紫微星下凡之日,此子命宮主星為紫微,日后必是一代帝王。”
“王大人此言未免太過武斷,姚妃腹中是兒是尚未可知,若說命宮紫微,委實太過可笑。”溫天神淡然,開口道。
王大人聞言,遂對著袁崇武跪了下去,拱手道:“啟稟皇上,微臣萬萬不敢欺君罔上,若皇上不相信微臣的話,可將欽天監的人全部召來審問,紫微星下凡乃是天象,并非人力所為,還皇上明察。”
袁崇武不聲,言了句:“朕曾聽聞,古時宮中亦有紫微星下凡之事,不過俱于皇后宮中,姚妃位于妃位,紫微星若真下凡,依著的位分,怕是沒這份福氣。”
“皇上,此事事關國本,再說后位懸空已久,紫微星下凡,對大梁來說自是可遇不可求的喜事,微臣斗膽,請皇上將姚妃娘娘立為皇后,以換我大梁國泰民安,國祚永存。”
禮部侍郎當先走出,對著袁崇武深深一揖。
諸人皆知袁崇武對玉芙宮娘娘疼若心肝,早有心立其為后,只不過一來姚氏為前朝公主,二來膝下無子,三來自建國后,袁崇武一直忙于豫西戰事,立后之事便一拖再拖,如今欽天監的人既能將紫微星下凡一事端了出來,便等于是袁崇武告知滿朝文武,要將姚蕓兒立為皇后。
Advertisement
近年來,袁崇武大權盡攬,鏟除異己,培植自勢力,如今的朝堂與他登基時自不可同日而語,朝臣最善于討得皇帝歡心,見欽天監如此一說,俱心中了然,戶部、工部、兵部,紛紛走出人來,對著袁崇武拜了下去,懇請皇上立后。
唯有溫天一派人卻按兵不,未幾,就有人上前,對著袁崇武道:“皇上,玉茗宮安妃娘娘乃皇上發妻,又為皇上誕下二子,皇上若要立后,玉茗宮娘娘于于理,都是皇后的不二人選,還皇上三思。”
話音剛落,朝臣中亦是有不人紛紛跪倒,對著袁崇武齊聲道:“請皇上三思。”
袁崇武著滿朝文武,眼底閃爍,道:“紫微星下凡,乃是天意,朕為大梁皇帝,又豈能逆天而行?”
袁崇武話音剛落,不待滿朝文武出聲,就見一個侍臉慘白,匆匆奔了過來,“撲通”一聲向著袁崇武跪了下去,渾瑟瑟發抖。
“啟稟皇上,宮里出事了,安妃娘娘在玉芙宮里中毒亡,姚妃娘娘……也不好了……”
侍的話說完,大殿里便如同炸開了鍋一般,文武百面上皆失,而袁崇武則豁然站起子,他的眸心黑得駭人,甚至連一個字也沒說,便大步沖了出去。
玉芙宮中,腥氣極濃,待那抹明黃的影趕至時,整座宮室的宮人俱黑地跪了一地,每個人都是面如白紙,直哆嗦著,說不出話來。
袁崇武周被一層濃烈的戾氣籠罩著,他不曾對地上的宮人看一眼,橫沖直撞往殿闖,不時有宮人撲在他的腳下,聲道:“皇上,您不能進去,娘娘正在生產,會沖撞您……”
男人并不理會,一腳將宮人踹開,殿中的人聽到靜,每個人的臉都難看到了極點,就連牙關都打起了戰,紛紛跪了下去。
Advertisement
后殿中的腥氣比前殿還要濃郁,撲面而來,讓人作嘔。袁崇武站在了那里,他似是怔住了,眼睛死死地盯著床上的姚蕓兒,濃稠的從的下不斷地涌出來,沾得到都是,太醫與穩婆俱是雙手紅,就連襟上也是通紅的一片,更不消說那床褥與錦被,更是早已被水打,珠子一滴滴地落在地上,發出一陣急促的“嗒、嗒、嗒”聲。
“皇上,娘娘中了劇毒,這會兒子,怕是……兇多吉了啊皇上!”張院判子抖得如同秋風里的落葉,一張臉比死人還要難看,跪在地上不住地叩首。
袁崇武一語不發,了拳頭,竭力讓自己冷靜,可子卻還是抖了起來,不他控制地抖。
床下已凝聚了一大攤鮮,待男人的朝靴踩上去,讓人極清晰地察覺到那一抹黏膩,袁崇武眼前一黑,俯將床上的子一把抱在了懷里。
“蕓兒,醒醒!”他的大手拂去子臉頰上的發,就見那一張小臉煞白煞白的,眼睛閉,周冰涼,眼見著氣若游,活不了。
袁崇武驚痛到了極點,心頭活生生地被人撕扯得不樣子,他回過頭,對著匍匐于地的張院判啞聲道:“過來,為娘娘止!”
張院判抬起頭,額上滿是汗珠,慌道:“皇上,微臣已想盡了法子,都不能將娘娘下的止住,娘娘懷胎九月,若要止,也需將胎兒娩出,如今這形,微臣……微臣實在是沒法子啊!”
袁崇武將姚蕓兒攬在懷里,他的臉鐵青,整個人繃著,聲音卻冷到了極點,讓人聽得清清楚楚:“那就將孩子取出來。”
張院判大驚失,道:“皇上,若是強行將胎兒取出,孩子定是不保,還皇上三思。”
Advertisement
“朕不管你用什麼法子,你若救不活,朕要你全家陪葬!”袁崇武雙眸紅,每一個字都寒意森森,落進張院判耳里,讓他全一涼,冷汗滾滾而下。
西郊,皇長子府。
溫珍珍倚在人榻上,待心腹丫鬟走進后,頓時從榻上支起了子,道了句:“怎麼樣了?”
那丫鬟福了福子,低語出聲:“小姐,安妃娘娘中毒亡,尸首已被抬回了玉茗宮,大皇子和二皇子俱在那守著,而皇上卻一直留在玉芙宮中,誰都不見。”
溫珍珍眼眸一跳,對著道:“可探到姚妃的形?”
“聽說姚妃如今只剩下了一口氣,毒已遍布了全,從子里流出來的,幾乎要把整座玉芙宮都淹了。”
溫珍珍聞言,角便浮起一笑意,道:“如此說來,姚妃這一次,就算是大羅神仙也難救了?”
“可不是,太醫署的人全扎在玉芙宮,也毫無法子,據說皇上大發雷霆,說救不活姚妃,就要整座太醫署的人陪葬。”
溫珍珍冷哼了一聲,似是不以為然,可想起宮中的變故,心頭終究是舒暢的,未過多久又微笑起來:“我那可憐的婆婆雖說目不識丁,又是庶民出,可這手腕倒實在是高,既除去了姚氏母子,又給皇上來了個死無對證,對自個兒也真能狠下來心,不得不讓人佩服。”
那丫鬟見主子心極好,遂道:“小姐,安妃說到底也是大皇子的母親,如今故,按說您也該進宮為守孝,要不要奴婢服侍您更進宮?”
溫珍珍搖了搖頭,整個子都舒坦地向著人榻上倚去,淡淡道:“不必了,咱們再等一陣子,看看形再說。”
不等那丫鬟答應,又是一陣腳步聲匆匆而來,溫珍珍抬了抬眼皮,就見一個嬤嬤氣吁吁,先是對行了一禮,繼而道:“夫人,方才從宮里傳來了消息,說是姚妃娘娘在玉芙宮誕下一子。”
Advertisement
“什麼?”溫珍珍倏然起,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對著那嬤嬤道,“不是說姚妃奄奄一息,只剩下了一口氣了,上哪生的兒子?”
那嬤嬤心驚跳,囁嚅著言了句:“夫人息怒,這其中的關竅,老奴也不知曉啊。”
溫珍珍從人榻上走下,心頭怦怦直跳,道:“那姚妃眼下如何了?”
“姚妃娘娘失過多,怕是拖不了多久了,皇上跟瘋了似的,寸步不離地守著姚妃。禮部那邊,已悄悄備起了后事。”
溫珍珍聽了這話,心頭方才舒了口氣,只笑得涼涼的,道:“這便是了,任是皇上有心將立為皇后,也要瞧自個兒有沒有這個福氣,妄想著當開國皇后。”說到這里,溫珍珍頓了頓,繼而輕啟朱,冷冷地吐出了三個字來,“也配。”
玉芙宮中,燭火通明。
“皇上,娘娘上的毒已侵臟腑,又加上生產時失過多,微臣只怕……娘娘撐不到明日了,還請皇上暫且回避,讓宮人為娘娘梳洗一番,也好……干干凈凈地上路。”
張院判艱難地將這句話說出,頭只垂得低低的,甚至連瞧都不敢去瞧袁崇武一眼。
男人一不地守在床前,對張院判的話置若罔聞。
“皇上……”張院判久久不見男人出聲,終大著膽子,又喚了一句。
“滾!”袁崇武終是開了口,這一個字低啞重,似是在竭力忍,隨時都會發。
張院判不敢多待,跪著叩首,畏畏地退了下去。
后殿中的腥氣依舊凝重,消散不去,姚蕓兒無知無覺地躺在那里,臉白如雪,沒有丁點人。
袁崇武將的子小心翼翼地抱在懷里,因著流了太多的,的子涼得如同一塊薄冰,袁崇武將近自己的口,自己則俯下子,將臉龐埋在的發間,沒有人能看清他臉上的表,他伏在那里,半晌都沒有彈一下子,唯有肩頭卻輕微地。
玉芙宮后殿,娘抱著新生的小皇子,卻是一臉憂,道:“這孩子落地三日了,卻連一口都不喝,可怎麼養得活。”
另一位娘聞言,也嘆道:“可不是,小皇子出生至今,皇上只顧著姚妃娘娘,一眼也沒來瞧過,這孩子倒也當真可憐。”
娘抱著懷中的嬰兒,見孩子生得濃眉大眼,唯有面卻泛著青紫,與尋常嬰兒大有迥異,讓瞧著便憐惜起來,輕聲道:“太醫說小皇子在母里沾上了毒素,解毒的藥要咱們喝下,化喂給孩子,可這孩子一直不吃,怎麼是好。”
兩人說起來,俱是憂心忡忡。小皇子出生至今,呼吸一直都是微弱的,落地三日,竟是從未哭過,宮人們幾乎不敢合眼,日夜守在孩子旁,似是生怕他隨時會去了。
“哎,娘娘今日怎麼樣了?”當先那個娘一面輕拍著孩子,一面小聲開口。
那一位娘亦低了聲音,道:“能怎麼樣,我聽人說,那鴆毒只需一小塊指甲大,就能毒死一整頭牛,安娘娘都已被毒死了,咱們家娘娘如今能保得命,也算是老天開眼,玉芙宮上上下下,都該念聲阿彌陀佛了。”
當先那位娘便一聲輕嘆,用勺子沾了些,輕輕順著孩子的溜了一點點進去,孩子小,又不肯吃,娘們只得將下,隔一小會兒便給孩子里順一點兒。
兩個娘嘀嘀咕咕,盡是說些宮中瑣事,未幾,便有太醫署的太醫來為小皇子號脈,兩人連忙將孩子小心翼翼地抱了出去,一點一滴,無微不至。
玉芙宮,后殿。
姚蕓兒仍一不地躺在那里,整個人單薄得如同一陣輕煙,仿佛輕吹一口氣,就能將給吹跑了一般,再也凝聚不到一起去。
袁崇武寸步不離地守在床前,解毒的藥已灌了下去,可姚蕓兒仍不見毫氣,便如同吊著一口氣,讓人膽戰心驚。
“娘娘究竟何時能醒?”袁崇武回眸,對著跪在地上的太醫言道。
“回皇上的話,鴆毒乃天下第一奇毒,絕非朝夕可解,微臣已仔細察看過娘娘先前用過的茶點,發覺那一壺螺茶中便藏有鴆毒,所幸娘娘當日只飲了半盞,毒發時又有腹中胎兒分去了些許毒素,娘娘這才保住了一命。”
袁崇武攥了姚蕓兒的小手,的小手宛如冰塊,仿佛一便會碎了。他斂下眸心,低聲言了句:“你也不知何時能醒?”
那太醫一怔,繼而深深俯下了子,恭聲道:“臣不敢欺瞞皇上,娘娘的臟腑已被毒素侵蝕,未有三年五載,定無法將余毒解清,再有,臣只怕即便娘娘日后醒來,也是……”
“也是什麼?”男人神一變,聲音里亦嚴峻起來。
那太醫咽了咽口水,躊躇著開口:“娘娘昏睡已久,臣……只怕鴆毒會侵蝕娘娘心智,古籍上曾有記載,前朝有位公主曾誤食鴆毒,待其醒來后,已形如癡傻,宛如孩,就連周遭的人,都全然不認識了。”
袁崇武聞言,眸心的頓時暗了幾分,一字一字地啞聲道:“你是說等娘娘醒來,什麼都不記得,就連朕,也不認識了?”
那太醫心神一凜,道:“微臣不敢肯定,一切都要等娘娘醒來才能得知。”
袁崇武凝視著床上的子,口萬刃裂心般地疼,他沒有再說話,只對著太醫擺了擺手,示意他們退下。
待后殿只剩下他們二人時,袁崇武微微俯下子,出糲的手指,輕上姚蕓兒的臉龐,他的嗓音已嘶啞,低語了一句:“蕓兒,你真會忘記我嗎?”
玉茗宮。
溫珍珍一縞素,秀發盡數盤在腦后,做婦人裝束,當踏進玉茗宮時,就見靈堂前跪著兩道影,整座大殿清清冷冷,竟連個服侍的宮人都遍尋不見,只有袁杰與袁宇。
見到溫珍珍,雙眸通紅的袁宇則掙扎著從地上站起子,上前恭恭敬敬地喚了一句:“大嫂。”
溫珍珍頷首,一張臉猶如清雨梨花,無限哀婉,聲音滴,滿是凄清:“怎這大殿空空的,別的人呢?”
袁宇聲音沙啞,道:“宮人都被哥哥趕了出去,母親靈前,有我兄弟便夠了。”
溫珍珍眼圈兒一紅,見袁杰子跪得筆直,即便聽到自己的聲音,仍直地跪在安氏靈前,不曾回過頭來看自己一眼。
聲音清脆,在這大殿中顯得格外清晰:“難不這幾日,父皇都不曾來瞧過母妃一眼?”
袁宇心口一酸,道:“姚母妃危在旦夕,父皇守在玉芙宮,也是人之常。”
溫珍珍舉起帕子,抹了抹眼睛,道:“妾聽說母妃與姚妃娘娘是同時中毒,妾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何只有母妃送了命去,姚妃娘娘卻能誕下麟兒,母子均安。”
猜你喜歡
-
完結1140 章

穿書之貴女咸魚日常
十三年后,那個科考落榜的少年郎李臨拿著一塊玉佩上門來要娶晉寧侯府的千金小姐。帝城轟動,紛紛在猜想晉寧侯府哪個千金倒了八輩子的霉,要嫁給這個癩蛤蟆。穿書的蘇莞暗搓搓地想,大伯家的嫡女是重生的,二伯家庶女是穿越的,她這個開局第一場就被炮灰掉的小炮灰,要智商沒智商,要情商沒情商,算了,咸魚點,還是趕緊溜吧。可是沒想到,她...
206.7萬字8.18 27162 -
完結1433 章

醫妃張狂:厲王靠邊站!
前腳被渣男退婚,厲王后腳就把聘禮抬入府了,莫名其妙成了厲王妃,新婚夜差點清白不保,月如霜表示很憤怒。老虎不發威,當她是病貓?整不死你丫的!…
221.3萬字5 93988 -
完結622 章

重生後,將軍她被冷戾王爺嬌寵了
她是北國赫赫有名的女戰神,守住了天下,卻防不住最信任的人反手一刀。 被渣男親妹算計隕命奪子,慘死重生后成了逃命的小可憐,轉頭嫁給了渣男他弟。 外阻南境,內聯七絕,天下消息盡在她手。 這一次,渣男的江山,狠毒妹妹的狗命,她全部都要! 她手段果斷狠辣,卻在那個清冷病弱的王爺面前破了功 磕磕巴巴:“我,我也不清楚是原來孩子是你的......” 冷戾的男人眼眶通紅:“你的前世是,今生也是我,生生世世我都不會放過你。 ”
110.5萬字8 34883 -
連載2433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于盡,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不過,不是不能人道嗎?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只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里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542.7萬字8.18 13890 -
連載50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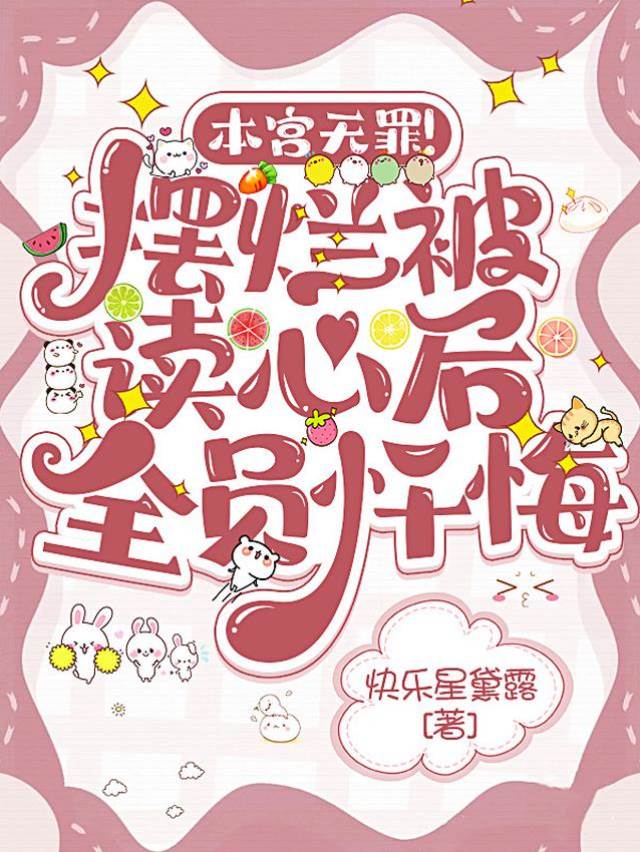
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
微風小說網提供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在線閱讀,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由快樂星黛露創作,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最新章節及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就上微風小說網。
85.5萬字8.18 3813 -
完結200 章

開局當兵發媳婦,我激活了斬首系統
穿越到古代,別人都因當兵發媳婦逃跑,就我激活了系統先挑了個潛力股,別人拼命練武殺敵攢軍功想當大將軍,我殺敵變強還能召喚千軍萬馬,一統天下不就是我的人生巔峰嗎?
37.3萬字8 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