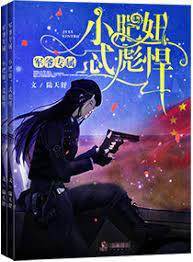《大唐小郎中》 第282章 死而復生(不想看推理的請跳到285章)
大問:「公子是有證據還是推測的?」
左道:「當然有證據。我已經仔細檢驗過婦死亡現場,發現婦是被人拉上房梁類死的,而不是自己上吊而死。因為套住脖頸拉人上吊而死,人的重量會讓繩索或者在房樑上產生很明顯的痕跡。而自己上吊的話,房樑上不會有這種痕跡。我檢查了房梁,找到了清洗的新鮮痕。說明是被人拉上去弔死的,而不是自己套好繩索上吊的!」
大臉蒼白了,不僅僅是因為傷:「就算是吧,也不能說是我把拉上去弔死的啊,我一個人能把拉上去弔死嗎?」
「是不能,所以你找了逃兵做幫手。」
「你不是說逃兵膽子很小嗎?他怎麼敢幫我殺人?」
「我又不在場,我怎麼可能知道這麼詳細?不過我相信你有辦法,比如威脅他。」
「威脅?我一個人怎麼威脅他?」
「把柄啊。」左道,「所有的人對了禪大師的財都有興趣,包括他的五眼六通佛珠。你或許唆使他潛了禪大師屋裏盜竊,然後故意吵醒大師,逃兵慌之下,用香爐砸死了他,你就用這威脅他讓他幫你殺死婦。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實可能不是這樣的,到底是怎麼讓他幫了你,我不清楚。需要你來告訴我。」
「你這一切都只是推測,你說我殺人,有真憑實據嗎?」
「證明你直接殺死婦的證據,說實話沒有。但是,我有你殺死逃兵的直接證據!」
大軀一,勉強笑道:「公子認為,那逃兵也是我殺的?」
「沒錯!你夥同逃兵在婦住的禪房裏弔死婦之後,趁逃兵不備之機,就像你殺死婦的丈夫一樣,從後面用箭突然進他的後腦,死了他。——這箭做白羽穿甲箭,可以穿鎧甲,非常鋒利,以你的力量已經足夠死他了。然後你將拖到了院子裏。」
Advertisement
「你有能證明我殺了那逃兵的證據嗎?」
「當然有!」左道,「我在檢查逃兵撲到在院子裏的的時候,抬起上半,在他的下,發現了你殺人的鐵證!」
大咬咬牙:「什麼鐵證?」
「一雙腳印!」
「腳印?」
「沒錯,留在雪地上的腳印!院子裏的積雪了禪大師掃過,落下來的雪鋪得不太厚,所以留下來的積雪足夠讓人留下清晰的鞋印。——你當時拉著的雙肩,倒退著將拉出房門,一直拉到院子裏。你看見了將你留下的腳印都抹平了,你以為等一會你走開之後,天上飄落的大雪,很快會掩蓋掉你留在院子裏的其他鞋印,沒人知道你來過這裏。所以你安心地回房睡。可是你忘了,你是抬著雙肩拖出來的,放下時,肩膀位置你留下的鞋印,卻沒有被抹掉,讓我辨認出這是一雙小的人腳印!不可能是我們幾個大男人的大腳丫留下的。」
左上前兩步,瞧了瞧大的一雙小腳:「當時活著的人,就你跟舍妹,舍妹一直在我邊,所以只有你!——沒有挪過,這雙鞋印現在肯定還在,要不要用你的鞋子比比?」
「那婦的鞋子跟我差不多大,為什麼不能是那婦?」
「當然不是,就按你偽造的現場來說,婦在屋裏死了院子裏的逃兵,但是,婦如何在逃兵下留下一雙鞋印?死了逃兵,然後出門抬起,在他肩膀下踩出兩個鞋印來?」
「可以先走到院子裏跟逃兵說話,然後回來,拿弓箭死逃兵,逃兵撲到,不就正好蓋住了那鞋印了嗎?」
左笑了:「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好,我告訴你,我已經很仔細地觀察了,肩膀下面的那雙鞋印裏面很乾凈,表面很,連一朵雪花都沒有,如果像你所說,先出去跟逃兵說話,再進屋拿弓箭死逃兵,昨夜一直在飄雪,都覆蓋了雪花,鞋印里怎麼會沒有一朵雪花呢?」
Advertisement
「這個……」
「還有,如果逃兵是站著被婦從後面一箭死,以他的重量,撲到在雪地里,下面的鞋印絕對會被震得很凌,而不像現在那樣完整,這隻有輕輕放下才會如此。由此可以推斷,逃兵是被人殺死之後,拖到院子裏來的。——勘驗現場的時候,我發現婦屋門方向到之間,落雪比其他地方淺,這是因為拖帶走了部分積雪,形了一個凹槽,你當時沒有注意這一點。以為飄落的雪花會幫你掩飾拖痕,但沒想到積雪厚度不一樣,讓我發現了是被拖出來的!」
大苦笑:「公子觀察得好仔細。還有一點,除了我,那個塌鼻子人了我的東西跑了,為什麼不能是?」
「不可能是!」
「為什麼?」
「因為早就被你殺死了。」
大勉強出一笑意:「公子又是推測?」
「不是。」
「那公子是有證據了?」
「是的。」
「什麼證據?」
「我找到了塌鼻的,」左拄著拐杖走到那塊覆蓋著佛祖塑像的那塊巨大的黑綢布的左邊,「你把藏在了這裏!」抓住黑綢往上一,下面赫然一,眼睛瞪得溜圓,脖頸上死死纏繞著一白綾。正是失蹤的塌鼻!
左冷笑道:「剛才你在跟禪房掏空老者的的時候,我並沒有閑著,我把整個大殿裏外都搜索了一遍,因為我知道,你要殺塌鼻,最好的地方就是大殿裏,最好的時機就是我和小妹離開的時候,而以你的力量,你不可能把扔得很遠,也沒有這個時間,只可能藏在近,我沒有費很多時間,便在這下面找到了的。另外,我還在手心裏找到了一件東西,證明了兇手就是你!」
Advertisement
「什麼東西?」大子開始發。
左從塌鼻攥著的手裏輕輕出了一頭髮,一很長的頭髮,走過來,亮給大瞧:「這頭髮很長,山上其他人的頭髮都沒有這麼長的,唯獨你。如果你認為不是你的頭髮,可以扯一下來比比,再把其他人的頭髮扯下來比比,就知道了。——幸虧大殿裏線昏暗,你才沒有發現被你勒死之前扯下的這長發。」
大子一,差點癱在地上,強撐著扶住供桌,著左苦笑:「是,是我殺了他們四個,但是,了禪大師不是我殺的,也不是我指使逃兵啥的。我承認我也有心殺他,但是沒等我手,他就已經被人砸死了。」
左冷笑:「行了,做了就做了,承認了四個,為什麼不承認這一個?」
「因為真的不是我殺的。」
「那你是如何讓逃兵幫你殺死婦的?」
「我說了,你是不是可以饒我命?」
「我剛才也說了,只要是你幫做一件事,做得好,我可以不殺人。」
「好!你答應了的,不準賴皮!」
「我說話自然算話!」左角有一抹不易察覺的譏笑。
大沒有看見,理了理長長的披散在腦後的秀髮,說道:「我先挑逗他,讓他慾火中燒,這時候的男人,你讓他幹什麼都可以,更何況我譏諷他沒吃到羊惹了一,他就說想去把那婦了,我就說可以,這時候去用強,那婦會破罐破摔順從的。我就假裝過去道歉,騙開了房門,然後逃兵就進來了,先是賠罪,那婦只是低聲哭泣,然後逃兵就手腳,婦便讓他滾。」
左嘆道:「這子雖然最初為了一口饃饃,忍了這逃兵的猥,但是到了真格的時候,還是很貞烈的。」
Advertisement
「是啊,」大道:「我示意逃兵用強,逃兵就抱住,拚命掙扎,但是沒有喊,我故意倒了桌上的燈,屋裏很黑,我就乘用事先準備好揣在懷裏的白綾掛在房樑上,一頭套在脖頸上,使勁往上拉,屋裏黑逃兵不知道,還以為是要爬起來,就抱著的兩手,我就這樣把婦半吊著勒死了。逃兵不知道婦已經死了,還以為順從了,就開始的,我進來的時候帶了一支箭,趁那逃兵向婦賠罪的時候,瞧瞧藏在屋裏的,取出來扎死了這逃兵,後面說的跟你說的一樣,我把婦拉到橫樑上假裝上吊,又把逃兵的拉到院子裏,然後關上門回房睡覺了。事就是這樣。」
「那了禪大師是誰殺的?」
「不可能是逃兵,因為他出來之後就跟我進我房間了。可能是那老者吧。他也垂涎大師的佛珠、糧食和寶貝。或許是乘想大師的佛珠,結果被大師發現,就殺死了他。」
「嗯……,應該是這樣了。兇手已經伏法,也算是因果報應吧。」
大哀求道:「公子,你答應了我說了實之後,你就不殺我的,這就放了我吧?」
「你還沒幫我做事呢。」
「做什麼事?」
「我要你幫我做的事,其實就是你殺這些人的原因。——了禪大師寶藏!」
大強忍劇痛,嫣然一笑:「我明白了,原來公子才是真正的高手,你也垂涎大師的佛珠、糧食還有那一箱寶貝,你早已經察我做的一切,卻不聲裝傻,讓我替你殺人,而且,你還把自己的妹子都殺了,真是夠狠。」
「這無毒不丈夫。行了,咱們別廢話了,起來做事吧。」
「要我幫你做什麼?」
「進地窖啊!」左掏出一串鑰匙,「這是從了禪大師上找到的地下室的鑰匙,我得打開地下室,才能取到糧食和其他寶貝,但是,了禪說了,這地下室是他一位擅長機關的師兄修建的,裏面布有機關,當初是用來防範強盜的,雖然先前大師說過,裏面的機關已經關閉了,可是我這人生多疑,不敢相信人,所以,讓你進去探探路。」
大臉煞白:「公子,求你了,我不想死,你說過的,我說了實,你就饒過我的!」
「說了,我也說了你幫我做了這件事之後啊。」
「可是你說了不殺我的,而我進那地窖,肯定會死的!」
左笑了:「沒錯,我是說了不殺你,——是我不親自殺你,要是機關殺死了你,我就沒辦法了。那是你命不好,不過,你一口氣殺了四個人,也算夠本了。如果地窖要了你們命,那是你命該如此。如果地窖真的被了禪大師關閉了機關,你僥倖沒有死,那是你命大。」
大想了想,道:「要是我進了地窖沒有死,你是不是就不殺我了。」
「是的,不過為了安全,我會把你趕出寺廟,讓你在山頂自生自滅。」
「那不是跟殺了我一樣!」
「你沒得選。除非你寧願讓我一刀刀活剮了你。我連我妹子都能殺,千萬別懷疑我的這句話。」
大慘然一笑:「我信,你夠狠!你做得出來。好,我認命,反正跟你說的一樣,我殺了四個了,也夠本了。再說,老天爺也未必會收我!走!」接過左手裏的鑰匙,又道:「我一條傷了,怎麼走?」
左走到供桌旁,一刀劈斷了供桌的一條扔給大,然後把手裏的繩索扔過去:「套在脖子上勒!」
大照做了,撿起那供桌撐著,拖著那繩索,一瘸一拐走進了禪的禪房。左握住繩索另一頭,跟在後面。
禪房裏,了禪的依舊躺在床上,腦袋扁扁的,痕已經了暗紅。
大用鑰匙打開了禪房門,一手靠著牆壁,一手用拐杖在地上和牆壁四周著,包括頂部,完之後,這才往前一步,然後再。
就這樣一步一探,花了一頓飯工夫,這才走過了這短短的通道,進到了地下室里。
左拿了凳子坐在地下室口外,攥著那繩子瞧著。見平安地走進了地下室,也舒了口氣,道:「把箱子打開。鑰匙應該在那一串裏面。」
大一把把試,終於吧嗒一聲,把箱子上掛著的銅鎖打開了,小心地取下來,然後慢慢揭開那箱子的蓋子,往裏觀瞧。
這一瞧之下,大愣了,隨即仰天大笑,笑得甚至連眼淚都出來了。
「你笑什麼?」左奇道。
大回頭瞧著他:「想知道,怎麼不自己進來瞧?我都已經探查過沒有機關了,你這麼怕死啊?」
說著,大又走到那一堆糧食麵前,扯開了一袋糧食,便聽見嘩啦啦的聲音響,大又是發出一陣大笑,甚至笑得都彎下了腰。
地下室里沒有燈,而通道又比較窄,所以裏面很昏暗,左除了能看見大影外,看不清地下室的況,不知道到底在笑什麼。便道:「行了,你把箱子拖出來!」
「拖不!咯咯咯」
「那就把箱子裏的東西拿出來!」
「想看?好,我拿給你看!」大依舊笑著,彎腰從打開的箱子裏抱起一包東西,便在這時,就聽嗖嗖幾聲,大一聲短促的慘,便栽倒在地,扭了兩下,便一不了。
一灘鮮,慢慢地從下流淌了出來。
左大聲了幾聲,還是沒反應,便收手上的繩索,將大拉出了地窖,翻過來一瞧,大頭面部,腹部,著幾枚鋼鏢!已經氣絕而亡。手裏還抓著的東西,卻是幾件舊服。
左拿起那幾件服,滿是疑,扔掉服,取下繩子,點亮了禪房裏的一盞燈籠提著,拿著繩子一瘸一拐走了進去,小心翼翼來到箱子旁邊,將繩索套在上面,然後退出地窖,將那口箱子拉了出來。
原以為會很重,拉的時候才發現其實並不重,沒費多大勁就將箱子拉出來了。
左探頭看了看,裏面只是一堆服還有一些雜,用拐杖將服都挑了出來,卻什麼金銀財寶都沒有,連一枚銅錢都沒有。
左大失所,罵道:「他的,這老和尚騙了我們,什麼一箱寶貝,連個銅子都沒有!靠!我去看看糧食,別他娘的也是假的。」
他提著燈籠和單刀慢慢走進地窖,先看了一眼剛才大解開的米袋口子,頓時大吃了一驚,只見從米袋流出來的,哪裏是什麼大米白面,只是一堆泥沙!
左刷刷連續揮舞手裏單刀,挨著個將所有的米袋全都砍開,出來的東西,全都是泥沙,連一粒米都沒有!
他又衝到兩口大缸前,手撈了撈,兩口缸里只有表面一層是米面,下面也全都是泥沙!
左破口大罵:「他的,這個死禿驢,原來是騙我們的,害老子們自相殘殺,害得老子連自己的人都勒死了,真他娘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261 章

影視世界當神探
陸恪重生了,還重生到了美國。但他漸漸發現,這個美國并不是上一世的那個美國。 這里有著影視世界里的超凡能力和人物,他要如何在這個力量體系極其可怕的世界存活下去? 幸好,他還有一個金手指——神探系統。 一切,從當個小警探開始……
416.5萬字8.18 46115 -
完結358 章

嫡女無雙:惹火棄妃太搶手
手握大權卻被狗男女逼得魚死網破跳了樓。 可這一跳卻沒死,一眨眼,成了草包嫡女。 不僅如此,還被自己的丈夫嫌棄,小妾欺負,白蓮花妹妹算計。 你嫌棄我,我還看不上你;你欺負我,我便十倍還你;白蓮花?演戲我也會。 復雜的男女關系,本小姐實在沒有興趣。 和離書一封,你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 原以為脫離了渣男是海闊天空,可怎麼這位皇叔就是不放過她? 說好的棄妃無人要,怎麼她就成了搶手貨了?
81.3萬字8.09 94242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3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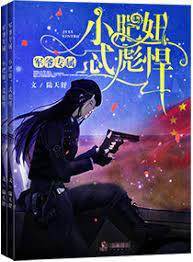
軍爺專屬:小肥妞,忒彪悍!
身為雇傭兵之王的蘇野重生了,變成一坨苦逼的大胖子!重生的第一天,被逼和某軍官大叔親熱……呃,親近!重生的第二天,被逼當眾出丑扒大叔軍褲衩,示‘愛’!重生的第三天,被逼用肥肉嘴堵軍大叔的嘴……嗶——摔!蘇野不干了!肥肉瘋長!做慣了自由自在的傭兵王,突然有一天讓她做個端端正正的軍人,蘇野想再死一死!因為一場死亡交易,蘇野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色誘……不,親近神秘部隊的軍官大叔。他是豪門世家的頂尖人物,權勢貴重,性情陰戾……一般人不敢和他靠近。那個叫蘇野的小肥妞不僅靠近了,還摸了,親了,脫了,壓了……呃...
96.9萬字8 14612 -
完結529 章
冷王追愛:萌妃輕點寵
一朝穿越,慕容輕舞成了慕容大將軍府不受寵的癡傻丑顏二小姐,更是天子御筆親點的太子妃!略施小計退掉婚約,接著就被冷酷王爺給盯上了,還說什麼要她以身相許來報恩。咱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躲躲藏藏之間,竟將一顆心賠了進去,直到生命消亡之際,方才真切感悟。靈魂不滅,她重回及笄之年,驚艷歸來。陰謀、詭計一樣都不能少,素手芊芊撥亂風云,定要讓那些歹人親嘗惡果!世人說她惡毒,說她妖嬈,說她禍國?既然禍國,那不如禍它個地覆天翻!
89.6萬字8 474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