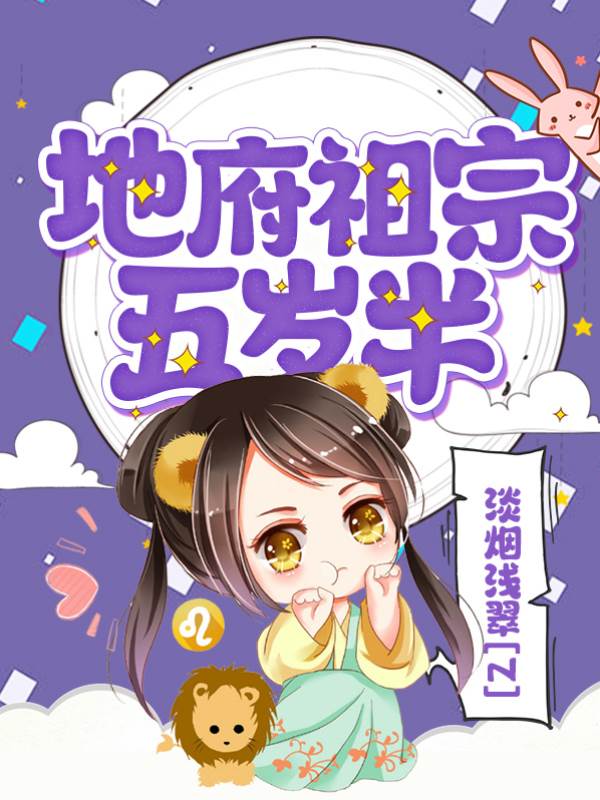《成為人生贏家的對照組[快穿]》 第257章 第兩百五十七章清穿文世界17
太子展示完,就安靜的坐著,此時他的表很平靜,心里更是毫無波,“知道,索額圖必死無疑,而兒臣......也肯定會失去這個太子之位。”
更甚者,還會被皇阿瑪懷疑,他有謀反之心,進而被誅殺都是有可能的。這是一步險棋!
太子恨嗎?他是恨的!
太子慌嗎?已經慌過了!
他原本的打算,利用五石散喚起皇父對他的父子之心,無論是康熙因為到了做太子的不易而憐惜,對他這個太子更好了,還是就此放棄他,讓他失去太子之位,都能解了目前的困局。
因為五石散是他主服用的,是他主給康熙的。
如果康熙下定決心要廢他,那也是他主遞了刀子,他當兒子的,已經這麼順著皇父的心意了,還要如何?
所以這是一出進可攻退可守的方法,依照太子的謀劃,他日后的日子會好過很多。
然而這一切,都被索額圖破壞了!
太子閉上眼,任憑他智計百出,豬隊友太多,也只能事不足敗事有余!
不,索額圖怎麼能是豬隊友呢,他是狼是虎,是野心的索相,唯獨不是豬。
他這個太子,只是他掌握權勢的工,而不是像索額圖自己說的,一切都是為了太子。
如果都是為了他,那在他再三表示自己無事之后,安心即可,索額圖也不會做出這麼膽大妄為的事來。
真以為憑著綠營那些人,就能殺進京城,殺皇宮?
太天真了,還是以為他這個當太子的,會里應外合,和他一起對付自己的父親?
即便這幾年,康熙對他越來越嚴苛了,但三十年的父子之不是假的,太子無論如何都做不到對皇父下手。
Advertisement
所以他行了!
太子就是太子,是康熙一手培養起來的儲君,認氣度,不比任何人差。
所以驚慌之后,他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決心,直接把紙條給了康熙。
康熙看著太子憔悴且平靜的臉,默默無語,里卻泛起苦。
怎會如此?怎能如此?他們原是最親的父子,原該最信任對方的,為何會變這樣?
康熙心里五味雜陳,繼而,他找到了突破口。
索額圖!索額圖!如果不是這臣賊子迫太子,太子不會走到如今的地步,所以都怪他,不殺他不足以平民憤!
當即,康熙就下令,嚴守東宮,就是一只蟲子,都不允許飛出來。
然后,他連夜派人去查看天津衛的綠營,發現真的有作,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拿下參將,游擊,守備等十幾位將領,統統捉拿歸京審問,至于綠營,已經換上了新的將領。
審問過后,雖然那些將領們都表示,他們沒參與任何反叛,有作是因為正常的練兵,別無其他。
然而康熙會相信嗎?他認為一定是索額圖還在,所以這些人才不敢講實話,所以直接在朝堂上發難,以結黨營私,圖謀不軌等多項罪名,把索額圖下了大獄。
赫舍里家嚇壞了,忙找人求,然而佟家,富察家等等都躲了,不去這個眉頭。
他們想要給宮里的太子遞信,信還沒有送出去,就被康熙下旨斥責,說他們隨意攀扯太子,不忠不義,讓他們在府里好好反省。
索額圖的大兒子找到赫舍里長泰,你是太子的親舅舅,和太子親近,幫幫我父親吧。
太子的親外祖父早就去世了,索額圖是叔外祖父,所以論關系,當然還是長泰這個親舅舅關系更近,但誰讓索額圖厲害的,權利大,是赫舍里家第一人,舅舅什麼的完全比不上,也被制的出不了頭。
Advertisement
現在索額圖倒了,赫舍里家人心惶惶,長泰沒什麼本事,一直很平庸,索額圖長子讓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于是也真的給宮里遞了消息,然后就被康熙劈頭蓋臉罵了一頓,還罷去了所有的差事。
這還不夠,康熙又下旨,命納蘭明珠審理索額圖一案,而赫舍里家從上擼到底,所有人都了白,凡是被彈劾有罪的,都下了獄。
太子在宮里,聽到這個消息,忍不住嘆氣,赫舍里家除了索額圖,就沒有一個聰明人。
都什麼時候了,還上躥下跳,是真的不知道死字怎麼寫嗎?
然而他現在如此敏,什麼也做不了。
太子忍不住苦笑,他這個太子當的,窩囊極了。
不過這一出之后,赫舍里家所有人都被嚇破了膽,小心翼翼窩在府里,什麼都不敢干。
納蘭明珠和索額圖是死對頭,那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仇敵,所以康熙指了他來主審這一案,意思很明顯,就是要索額圖死。
納蘭明珠作很快,不到一個月,就查清了真相,把滿滿一大疊證據,呈給了皇上。
康熙看完,當即下令,索額圖死,他的二子三子也被死,另外,索額圖一黨,也清查完畢,多數被殺,被圈,被流放。
至此,索額圖一案,告一段落!
可你以為,這就完了嗎?
殺了想殺的人,還清理了一批黨錮,康熙該松口氣了吧,該高興了吧?
并沒有!
太子在這個時候上書,表示自己這個太子實在無用,管不住臣子,讓外家生出狼子野心,威脅皇權。他不是一個合格的太子,更不是一個孝順的兒子。他無面對皇父,自請廢去太子之位。
康熙按下不提,也沒讓任何人知道。
Advertisement
這說明他還是下不了決心,但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就此嚴厲呵斥太子,說太子不該這樣,說明他心里的傾向,已經偏向了廢太子。
太子胤礽心里清楚,如果這次就這麼不明不白過去,那他就真的陷了泥潭,越掙扎反而陷得越深。
還不如一鼓作氣,讓自己離太子這個牢籠。
其實掙出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三十多了,人說三十而立,到了這個年紀,早該家立業,可他呢?
一輩子被困在皇城,就連邊伺候的下人,都是皇上的眼線,想出出不去,想做什麼都做不了。
還比不上大哥和弟弟們,好歹他們還能有機會出京,而在京城,他們是自由的。
現在他主辭,尚且能得到一份優容,不會被限制自由。
要是哪天皇父下定了決心,親自手廢掉他,那他只有被圈的命。
所以隨后的半月,太子每隔幾天,就上一道折子,折子容辭藻不華麗,但言詞間句句泣淚,說得康熙又傷又心酸。
就在他上第三道折子的時候,朝中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李地參奏一位修明史的閣學士,說他胡編造,不按事實編撰。
這事可大可小,往小了說,就是一位編史的員,出了一點差錯,改回來就好了。
可往大了說,這也是朝廷大事,因為前明是清朝打下來的,你這麼寫,是不是到大清皇帝的授意,故意掩蓋一些史事真相?目的是什麼?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原因?
這會顯得朝廷卑劣,要是被江南那些學子們知道,是要鬧起來的。
然而這位閣學士也覺得自己很冤枉,他哪里胡編造了?
這些都是有史料記載的,白紙黑字寫在書上,又不是他故意瞎寫。
Advertisement
“還請皇上明顯,這一段,我是參考了史錢文秉的記載小注,小注上寫的清清楚楚,某年某月某日,明英宗確實說過這樣的話,并解釋了前因后果。”
說著,他還請康熙派人去翰林院拿那本小注。
李地大怒,“虧你還是閣學士,難道不知道修史以正史為主,必須按照最正統的記載來,哪里能用這些不著調的小注。”
小注是什麼,就是史在正史記錄之后,覺得不夠準確,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補充寫完。
要說這樣的容,確實有六七可信,畢竟是人家親眼所見親耳所聽。
但加了自己的理解之后,就難免偏頗。
史的記錄為何簡潔明了,一般都是什麼時間,皇帝干了什麼,說了什麼,其他一概沒有?
因為這才是最準備的,即便當時皇帝是說反話呢,但史還就得這麼記,誰管你的真實意思是什麼?
如果都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記,那不是了套了,因為誰都可以加自己的理解,那還史記嗎?那還需要史嗎?
史只是見證者,老老實實記錄就行。
那為什麼在修史的時候,要參考史的小注,記錄等文本,是為了更好理解,但這類文本的可行度,又下降了一個檔次。
李地是正統的文人那一掛,認為史書就是史書,不該多加其他東西,和閣學士爭辯過后,就一狀告到了康熙這里。
而閣學士呢,則認為,正本和小注都是這位史自己寫的,并且這個小注能放在正本后一起編撰,就說明這小注的可信度上升到八,那便于理解,摘取一段,做個補充,有何不可?
兩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爭論不休,吵了好一會兒,才停下來,等待康熙下決定。
康熙先是安了兩位大人,覺得他們都沒有錯,這個可以酌理,既然人家史也沒有放到正本上,那他們也可以放后面的注解,不過閣學士可以據自己的理解,在注解后作出更加詳細的解釋,這是修史的目的之一。
康熙還強調,明史得修好,公論要采納,是非要明細,不然后人是要罵朕的。
他話鋒一轉,“為了表示重視,我會派一個皇子親自監督此事,各位老大人用心。”
至于是哪個兒子,康熙掃視了一圈,看向站在最前面兩排的皇子們,詢問道,“你們誰愿意領這個差事?”
太子不在,直郡王就是最大的,然而他不為所,修書的活和他有什麼關系,他只是一個武夫。
三阿哥看看大哥,又看看四弟,有點躍躍試。他覺得,這就是為自己量定做的,論兄弟之間,誰的文采最好,舍他其誰?
然而他一貫不敢冒頭,于是看四弟都不出面,腳出去又了回來。
老四當然不會出面,修史是個好活嗎?
是的,這是攢名聲的好活,能積累后名,后人但凡只要看明史,就一定繞不過修史的人,而現在某個皇子總攬,也一定能流芳百世的。
然而這有一個前途,四爺要的不是后世名啊!他對這些不是實務的工作,也不興趣。
說到底,修史面子上好聽,但一輩子就綁在上面了除非明史修完,不然修史的皇子,就干不了別的。
因為修史真的是一項既細碎又繁雜的活,就像剛剛兩位大人爭吵的。
他們有錯嗎?或者有誰不對嗎?沒有,他們的想法都沒問題,這就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誰的說法都講得通,然而想法不同的人卻是無論如何都說服不了對方。
皇上現在派人去,就是去斷司的。
可以預見,未來這樣的爭吵,還會有無數次,而皇子,就代表了皇上,在兩方間選擇一方。
能被提出來,就說明選哪方問題都不大,可斷司,尤其是這些文人之間,字眼上的司,還不是你說一就是一的,得先吵,吵得不耐煩了,選出一個,才能消停。
所以說,修史這個活,能把人所有的力都耗,再也干不了別的。
所以四爺了。
老五呢,他到是想接,皇上還不信他能辦好呢。
原因也很簡單,五阿哥是太后養大的,一直到六歲,進上書房,連漢話都不會說,文才方面,兄弟們之間,是最差的。
七阿哥,他的文才和五阿哥一樣不出彩。
八阿哥出彩,但他的想法和四阿哥一樣,修史就是出力不討好,還蒜皮,于是他也了。
九阿哥,他算賬好,做生意的本事一等一,另外他外文上面的語言天賦絕佳,修史,大概翰林院的學士們會嫌棄他銅臭味太重吧?
十阿哥不用說了,鐵憨憨。
十二阿哥從不冒頭,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剛婚,連上朝都是最近的事,能總攬這麼大的事?
所以,康熙的話直接在了這里,沒人接茬。
康熙瞧著下面,一個個低頭不語的兒子們,冷哼一聲,“怎麼?沒人敢接?”
這話一出,三阿哥立刻被激將了,跳出來道,“皇阿瑪,兒臣可以勝任,請旨辦差。”
康熙點頭贊許,“總算還有一個能辦事的。”
聞言,三阿哥立刻高興起來,志得意滿的看了兄弟們一眼,然后好心的建議道,“四弟的文學也不錯,兒臣舉薦四爺和兒臣一起。”
他自認為自己是好心來著,自從太子病了,四爺就一直躲著,雖然封了雍郡王,但從不敢冒頭。
三阿哥認為,這是避大阿哥的鋒芒呢,現在他這個當三哥的,就幫這個和他年齡相近的弟弟一把,給他一份差事做做,老這麼躲著也不是事。
然而四爺能氣死,老三就是個棒槌,什麼都不懂,還喜歡安排,遇到事了,又會回去。
打量誰不知道呢,老三就是怕自己應付不過來那些頑固的老大人們,所以找了四爺這個冷面將,讓他來斷司,然后老三在后面總攬。
他反倒為了幫老三跑的了。
四爺肯定不干,于是上前回稟道,“皇阿瑪,順天府河間府都上了折子,說年初到現在,接手了太多的山東流民,導致糧價居高不下,請求減免來年糧稅。”
這是第二件大事,原本不該四爺親自說的,雖然這件事是報給了戶部,而戶部由他總理,但還有戶部尚書和侍郎等人,他們肯定已經寫好了折子。
然而現在四爺顧不得了,再不給自己找點事干,就要被老三拖下水了。
康熙瞇起眼,“你覺得這事不行?”
“回皇阿瑪,如果況屬實,減免是應該的,不然來年百姓該沒有種子種了,因為他們買不起,但是減免,也沒用,如果朝廷不能發下糧種,沒得種,就算減了,百姓們也沒糧食啊!”四爺回道。
“那以你之見,該當如何?”康熙問道。
“首先得平糧價,讓百姓吃的起糧,買的起糧種,然后再考慮是否休養生息,減免一年的糧稅。”四爺回道。
“是這個道理,”康熙嚴肅的道,“但平糧價,需要糧食,糧食從何而來?順天河間的糧倉,經過一年的賑濟災民,已經清空了,周邊城鎮也一樣,總不能去江南調糧吧。”
四爺頓了頓,說道,“今年的秋收已經差不多了。”
戶部尚書立刻跳出來,“雍郡王,萬萬不可,今年的糧食已經有了更重要的安排,山東流民需要賑濟,邊關軍隊還不了糧食。您是知道的,這些都已經有了要的去,是一一毫都勻不出來,一點就要死很多百姓和將士的。”
這也是事實,四爺就總理戶部,當然知道這件事,并且還知道,朝廷拿不出更多的銀子購買糧食。
所謂錢用在刀刃上,在他自己和戶部各位大人的籌劃下,每一筆都很關鍵,關系到明年一整年的大事,實在拿不出來。
可順天河間兩府的百姓也不能不管,所以他直接上書到,“兒臣請旨,去順天河間平定糧價,至于所需要的糧食,兒臣已經想好了辦法。”
“哦?”康熙挑眉,他知道這個兒子,一貫是個做實事的,卻不知道,他居然還會這麼大包大攬?
“那你就寫個折子,把方法呈上來覽。”
“是,”四爺深吸一口氣,把一直藏在袖里的折子遞上去。
這是衛其軒連夜人送來的辦法,方法劍走偏鋒,是四爺從來不會用的。
然而這次,他決定賭一把!
只希方法是真的有用。
遠在溫泉莊子的衛其軒,微微一笑,他的方法,怎麼可能沒用?!
猜你喜歡
-
完結450 章

攝政王的掌中嬌重生了
【重生+團寵+甜寵】上一世,舒久安為救弟弟和外祖一家,被迫嫁給了攝政王。他們的開始並不好,可攝政王愛她、護她,視她為珍寶...她想和他相伴一生,白頭偕老。可最後,他們都成為了皇權爭鬥中的犧牲品。她從嫁給他開始,就成為了所謂親人手中一顆棋子,被算計利用。重來一世,她要當執棋之人,掌握自己的命運,守護在意之人...重要的是,與他在一起,全了上一世的夙願。
114.7萬字8.09 169931 -
完結24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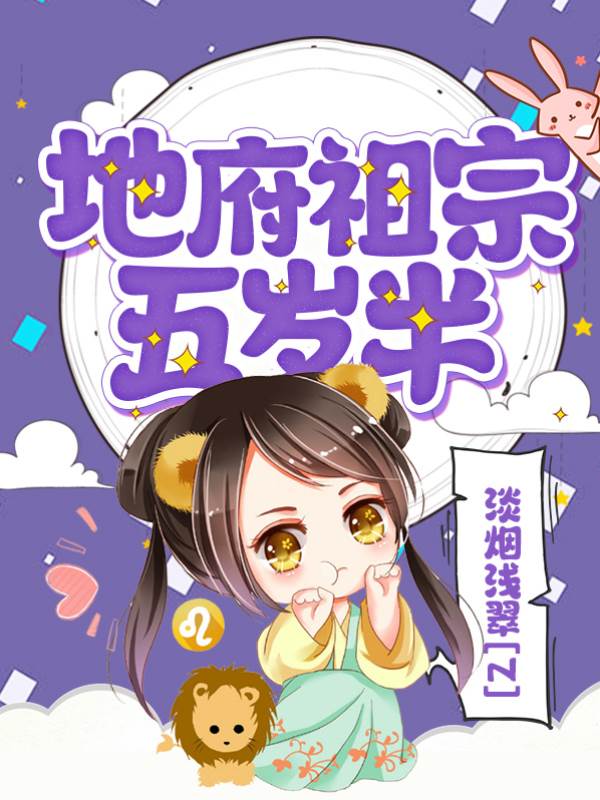
地府祖宗五歲半
天界第一女戰神虞紫薇渡劫失敗跌落凡間變成五歲小萌娃,被死對頭酆都大帝崔嵬撿回地府成了團寵的小公主。閻王被拔了胡須,判官的生死簿成了重災區,黑白無常成了小弟,鍾馗是保鏢。眾幽魂:地震了!地府怎麼塌了半截?閻王拍拍臉上的灰:別緊張,咱小公主練功呢!審問繼續。天界也遭了殃,太上老君的仙丹被盜,王母的瑤池被砸了個稀巴爛······眾仙家:酆都大帝,國有國法,天界有天規,交出你的女兒!崔嵬:我家寶貝我疼,你們誰都別想動她一根手指頭!玉帝:賢弟,眾怒難犯呀!你總得給我一個臺階下啊!崔嵬:那就懲罰我吧,反正我家小團子誰都不能欺負!轟隆一聲,天搖地動,原來是封印在九幽地府的妖王洛沉淵逃脫了。為了將功折罪,崔嵬帶著女兒來到人間化身王爺和郡主,暗查洛沉淵的下落。太後親自指婚,崔嵬無奈迎娶王妃。小團子卻…
43.3萬字8.18 3710 -
完結956 章

我在三國撿尸成神
劉毅穿越東漢末年,將能橫掃千軍,士能呼風喚雨,他卻獲得撿尸之術,從剛死之尸拾取各種物品,學技能,加屬性。他救下董卓,被收為義子,從此孝子劍在手,亂世重生,三國崛起,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190.3萬字8.33 215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